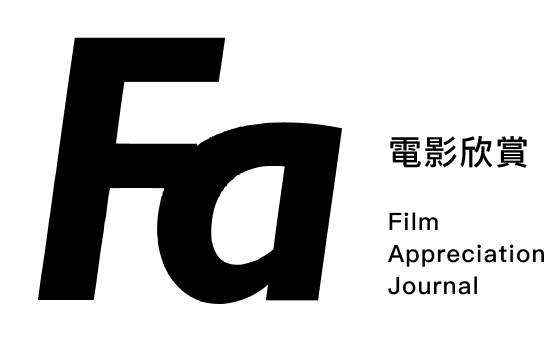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一切為明天》:在明天將臨前,追索未明的昨日軌跡

《一切為明天》:在明天將臨前,追索未明的昨日軌跡
今天的論述是為誰的明天?
一九八八年,國防部委託拍攝,由侯孝賢策劃、陳國富導演、吳念真編劇、蘇芮演唱的國軍形象廣告MV(早年稱「MTV」)《一切為明天》,絕對是台灣新電影乃至台灣電影史上迫切待解的一塊重要拼圖。尤其,這支當年隨「光輝十月」在三家電視台與全省六、七百家戲院播映的短片,早在誕生時即已承先啟後地超越單一影像文本的乘載:前接一九八七年的〈台灣電影宣言〉(「另一種電影」宣言);後引發「新電影之死」的論戰——評論人接力在隔月的《自立早報》副刊上進行專輯連載,並與其他報章雜誌的相關批評一同集結於迷走、梁新華主編的「戰爭機器叢刊」第三冊《新電影之死: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市》》(1991,下稱《新電影之死》)一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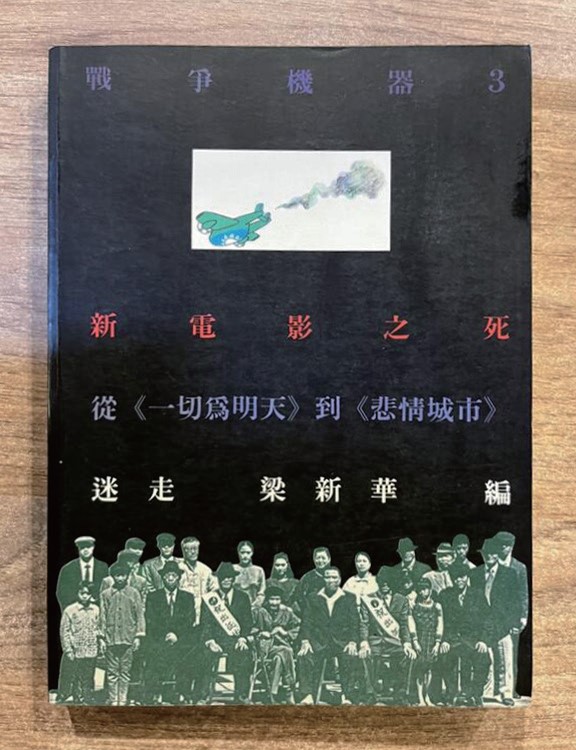
雖從影像文本的單點,擴延至「行動—事件—論述」的時間線,《一切為明天》的影像本身走向明天,卻弔詭地成了謎一般地存在;多年來只聞其名,不見其影。在這樣的時空斷裂下,我們或許得先自問:今日的重新閱讀可能會被放置在何種語境脈絡下作為詮釋工具?倘若本片適逢「新電影四十週年」現身,只是為了單向肯認新電影作為——容我借引陳傳興當年抨擊該片的用詞——黨國的「腹語」,理所當然地再賜死新電影,充其量也只是另一種研究論述上的「腹語」而已。更甚者,縱然影像檔案得跨越時空在今天復活,論述是否還能召喚出《新電影之死》當年的批判性,抑或只是在錯置的歷史脈絡下借屍還魂?尤其,除了「開明派可能是明天的保守派」❶、「忍見朋輩成新鬼」❷等警語言猶在耳,《新電影之死》的多位論者顯未止步於對個人乃至單一現象的討伐,而是在解嚴後一年即預示:反對政治於權力過渡階段的視野侷限,如何使得「文化成品為主宰集團服務」,❸以及民主化與啟蒙進程下的「解訊息」(desinformation)運作,如何「營建出一個腹語者的異聲喧嘩幻象」。❹故,在重新檢視此一藏品前,容我再次錯用卡維波當年的文章標題,我們皆須戒之慎之:昨日的《一切為明天》於今天的再出土,究竟「一切是為誰的明天」?
影像檔案的真面目或羅生門?
由外而內回到文本中,這個現存於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編號「D-000361」的藏品,為時長一分三十一秒的三十五毫米影像,共有兩份不同時間收入、內容相同的拷貝。全片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段落:首段以黑白影像追憶童年時光,男孩正懷抱從軍保家衛國的夢想;隨著主歌進入第二段,畫面轉為彩色,男童則已長成軍官。陸海空軍以直升機、軍艦與士兵列隊踢步前行的畫面相繼而出,並彰顯對科技的近用;副歌高昂地帶出全片第三段,場景卻從軍隊轉向了生活。軍官與親友群在肯德基中共食,眾人雖著便裝,長桌上卻擺著顯眼的軍帽。接著,大家在草地上抬頭望向畫外的軍機,小朋友們紛紛欣喜地向其揮手致意。值得注意的是,畫面正中央一位小女孩在漏敬禮之餘,後方的母親還特意推臂提醒。最後,貫穿全片的軍官手持軍帽入鏡,眾人合影留念。
全片以男孩的成長,同步國家的進步發展軸線外,亦貼合著國家治理的遞進軌跡;從首段畫紙上的理想藍圖,至中段實質軍事實力的展示,再到末段隱身於日常。其中,若以首尾兩次——自畢業班開枝散葉成數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合照做為切分,我們尤可辨認重複中的差異:戰機在首段末的畢業成年禮上,沿著攝影機運動方向低駛進畫面、穿越師生頭頂,卻在末段駛離跑道啟航,並於畫外為接續畫面中的親友群前瞻仰致敬;這一進一出除昭示國軍在國人心中留下永恆震撼後,將如後者搭配的昂揚歌聲所唱之——「我們會飛得更遠」,影片又透過各段間的畢業照過場,時時提示著初心。另一方面,拍下靜照的照相機亦如同軍機,從在場轉向缺席;首段末的鏡頭從畫面中攝影師與照相機的背後,緩緩向前推入,末段的親友群則朝向畫外微笑。於是乎,片尾眾人無論是望向天邊上帝視角般的軍機,抑或前方留影見證用的照相機,都是不存在對象的,其視線卻指認了畫外的權力部署。

在揭開檔案的真面目後,我們至少可以確認影片本身難以牽強附會任何(尤以《童年往事》為主的)新電影敘事或風格,亦無借題發揮或暗渡陳倉的蛛絲馬跡——它可以是任何人拍的。影像檔案的現身非但無法解開當年迷走在《新電影之死》章節引言中所形容的「羅生門」——亦即這件事的「內幕」究竟為何,反而留下更多未解之謎:首先,此一藏品究竟是不是該片的完整版本?本版收尾於該曲第一次副歌的倒數第二句,連點題的「走出從前一切為明天」都尚未唱到,歌曲結束得突然。而若參照《新電影之死》中的影像截圖以及迷走的文章描述,原應對映第一段末尾至第二段開頭的主歌B段,共有四句歌詞並未在本檔案中出現。甚至,該書所擷取的影格,在畫面與歌詞字幕的搭配上也與藏品有所出入。
倘若我們再查閱當年的報紙,各家媒體無論是在開拍前、剪輯階段或試片會後,皆陳述本片於三台播映的片長將為兩分三十秒,電影院短版則有開拍前的五十秒與剪輯階段的的八十秒二說;而最終的影像成品也不全然可見報導所揭露——以陸軍中校許錫林為主角,與五位後投入士農工商領域的鄉下兒時玩伴,於國慶日齊聚母校、述說往事,再次見證國軍戰機飛掠而過——的故事大綱。《聯合報》在試片會後、十月五日的報導中則指出,在侯孝賢和蘇芮的長時間溝通瞭解下,「最後剪輯出三支不同的片子,讓導演和歌者充分發揮個性。」
解嚴後政權的形象重塑
版本的變異雖指向政府相當然爾的主導與定奪,卻依然無法釐清生產關係。不過,《新電影之死》的論者也已為我們指引出政權正值轉型的重要時空背景:政治初擺脫「由上而下之單向訊息宣傳教育策略和單語論述」的「泛視」(panoprigue)系統,❺始擁抱資本主義的商品操作邏輯。❻《天下》雜誌在一九八八年底即以專文回顧,隨著前一年七月的解嚴正式開啟民間社會的全面監督,政府機關與國營事業勢必無法再漠視風起雲湧的聚眾抗議,「敞開大門,主動和民眾溝通,成為當務之急。」而從傳統教條式政令宣導口號,轉向與廣告或傳播公司的合作,「所要傳達的不單單是訊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改變這些機構的形象。」❼

其中,過去戒備森嚴的軍方可謂首當其衝,在頻頻被民意代表與媒體檢視批判下,竟成了這波新廣告潮的領頭羊。國防部負責文宣工作的總政戰部二處自二月起接連出招,一般認為其借重娛樂工業有兩個參照:一為前一年的軍教喜劇片《報告班長》大獲成功;二為再前一年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主演的《捍衛戰士》(Top Gun)成功帶動美軍招募熱潮。這可從國防部首波推出的兩支軍校聯招廣告短片之一,直接使用該片主題曲(卻也遭唱片公司抗議侵犯版權)得到證實。
而二月同期播映的另一支廣告MV主題曲〈年輕的喝采〉與〈擦亮你的名字〉,演唱者高明駿原為就讀國立藝專影劇科的緬甸僑生,初出茅廬竟一砲而紅,這奠定了軍方與唱片工業的合作基礎,後續推出的廣告MV包括:新格唱片林瓊瓏的〈大家都在說〉,滾石唱片趙傳的〈我的愛〉、吳倩蓮的〈我的驕傲,你〉,以及飛碟唱片張雨生的〈和天一樣高〉(慶祝八一四空軍節)、蘇芮的〈鋼鐵的心〉(慶祝八二三砲戰三十週年)等。

事實上,唱片作為文化商品拓展異業結合已行之有年,除了廣告歌曲外,八○年代亦致力與電影產業相互加乘,在快速變遷的視聽娛樂市場中殺出血路。比如蘇芮即交出〈酒矸倘賣無〉(《搭錯車》,1983)與〈親愛的孩子〉(《法外情》,1985)等代表作。國防部也現學現賣地讓《一切為明天》首次從影像與音樂雙管齊下,與過往廣告MV不同,明確主打「鄉土導演」與「現代歌手」兩張王牌。影像角色的突出另也可見於與《一切為明天》同在雙十國慶登陸戲院的新國歌片:該片經新聞局公開向民間甄選,最後採納中央電影公司(下稱中影)新銳導演張乙宸的「兒童篇」。在影音的整合下,《新電影之死》論者即針對倫理問題大書特書:比如迷走論及集體化、紀律化的軍事形象,如何在叛逆搖滾樂的包裝與天真兒童的點綴襯托下展現親和力,並在肯德基用餐等鏡頭下,擴展至對現代化生活的肯定;❽齊隆壬則論及影像中的「不在者」(the absent-one)如何無需被縫合至影像世界中,便已幽靈般地於畫面中無所不在。❾

黨政軍的權力鬥爭
不過,軍方對外的擦脂抹粉雖引起輿論迴響,對內改革的怠慢卻在在露出馬腳,箇中矛盾甚至於當年保守陣營的報章雜誌上引發檢討聲浪。而《新電影之死》論者雖相對提高批評層次,卻似乎低估了一九八八年政局的詭譎多變。彼時的政權轉型除了關乎解嚴後民主化與資本化並行的治理手段,更直接體現在蔣經國一月十三日逝世後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中。也就是說,因《一切為明天》的攝製正逢政權最不穩固之際,在重申如鐵板一塊的國家機器如何現身/隱身乃至對文化領域收編前,我們或許需先辨明政權內部的異質性,方能進一步指認一連串宣傳動作所牽涉的政治角力,甚或最終是誰藉此取得了權力展示的機會。
簡單回顧當年政局,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分別挺過一月的「代理黨主席」提案,以及七月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真除黨主席的艱難考驗,看似暫抵擋住蔣宋美齡勢力的介入,卻仍需與黨政軍與本外省等各方勢力明爭暗鬥;擁李的「主流派」與反李的「非主流派」將一路纏鬥至一九九○年的二月政爭與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尤其,我們知道當時實握軍權的並非身為三軍統帥的李登輝總統,而是一再延任邁入第七年的「強人總長」郝柏村。縱然他在權力移轉之際,多次對外宣誓效忠,並未顯露奪權野心,卻仍難消弭海內外各界對軍人干政的疑慮。比如鄭南榕即在郝柏村罕見接受《遠見》雜誌專訪後,持續嚴詞批評國防體制的紊亂與軍事統治的司馬昭之心。❿而在軍政與軍令尚未一元化下,參謀總長與總統及國防部長之間的從屬關係複雜,行政體系出身的李登輝顯難與「郝家軍」遍佈三軍的郝柏村抗衡,爾後方展開一連串的權謀計畫。
帶著這樣的認識再來檢視十月發布的《一切為明天》,李登輝在片中接續兩蔣的現身,雖理所當然卻也高深莫測。不同於兩蔣為黑白靜照「追憶」,彩色的動態影像在此宣告李登輝是權力核心的「現在進行式」。而在各別的影像再現中,第一段的蔣中正待鏡頭由左至右地橫移過一靜照,方在尾聲與(緊張嚴肅的)孩童微笑相望後淡出;第二段的蔣經國在下鄉巡視的一張多焦點構圖中,突兀地一閃而過;接續在三軍盡出後,李登輝幾近全身的入鏡則相反地作為絕對的視點中心,高站在緩緩行進的軍車上,向僅見帽沿的官兵回行軍禮,可謂確認了亂局中無庸置疑的軍事領導中心。
至於,掌管軍政的國防部在此階段率先以一波波的宣傳廣告削弱傳統軍方色彩,是否為有意為之的政治動作,仍待考據。惟,其中耐人尋味的是:時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並不直接從屬於總統,而是行政院長俞國華的下屬,並受蔣經國之弟蔣緯國任職秘書長的國家安全會議所牽制;兩人皆為外省籍親蔣勢力,雖在權力遊戲中相對被動,卻與李登輝分屬不同陣營。而鄭為元在隨後的二月政爭中,更成為唯二支持「主流派」的軍系中央委員,正式與「非主流派」的郝柏村等人分道揚鑣。

縱然我們暫難以追溯委任關係的來龍去脈,論述上卻勢必得重新反省:倘若直接在幕前顯影且可能為幕後推手的權力核心——李登輝前總統,可在今日被普遍視為「寧靜革命」與「台灣民主化」的推手;為何在幕後無實質政治權力且同樣展現體制內改革的台灣新電影,卻好似永劫不復地被鑲嵌於黨國標籤中置之死地?這似乎顯露歷史評價的雙標與失衡。
文化冷戰下穿梭的電影工作者
不過,一九八八年政治局勢的暗潮洶湧絕不僅於此。在微觀層次上聚焦黨政軍權力關係的如履薄冰後,我們接著可再將視角放大至「冷戰/戒嚴/反共」的框架,探究兩岸三地衝突張力的一觸即發。《新電影之死》中的陳文曾在文末直指此為問題的根本核心,⓫但除了思考最外顯的「國防」意義外,其究竟如何在這場文化事件中作用,實有待我們再行考掘。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其實尚未處理侯孝賢等人自身的選擇判斷;一方面他們事後始終沒有正面澄清為何接拍,因而真正惹火批評者,指控其逃避辯論與推卸責任。侯孝賢在詹姆斯.烏登(James Udden)二○○九年專書的訪問中鬆口,他「只是對『中影』被委託處理這個項目的朋友的個人幫忙」,否認帶有「突然的意識形態熱情。」烏登則順勢反駁批評者忽視了新電影從來沒有脫離體制,而是一個被迫改變的體制的最忠實展現、「一場由政治與經濟危機孕育與哺乳的藝術宣洩」,後被偏袒香港電影工業的「發行體制」所扼殺。他並提醒我們關注侯孝賢在脫離中影與新電影後,係因以海外市場與地位,回頭提升在台灣的影響力,創作生涯方能存活至今。⓬
所以,在解嚴與新電影結束後相應的創作策略下,侯孝賢等人究竟有沒有任何理由自願拍攝《一切為明天》呢?首先,國軍形象廣告的影像攝製其實不若唱片工業具循環的商業利益;後者除能累積知名度外,還可將高傳唱歌曲再灌錄至專輯中發行銷售。一位不具名的上校更曾出面解釋電影人其實皆未領片酬。⓭不過,詹宏志則在去年受訪時,坦言此一錯誤決定背後係因侯孝賢需要錢,在缺乏政治敏感度下,「誰找他他都很高興」,並確認新電影無法撼動「宏觀政策」,只能在微觀政策上作用的「低角度」文化現象。⓮不管何種說法為真,未全然投身廣告領域的電影人,應皆難憑單一個案取得維生或紓困外的金錢利益;而當我們再攤開侯孝賢一九八八年的活動軌跡時,亦可發現烏登所提示的重要過渡作品《尼羅河女兒》(1987),其實在侯孝賢國際能見度的鋪展上,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他幾乎整年都馬不停蹄地在海外各地奔走——除五月首度入圍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十月亦二度入選紐約影展,並獲邀至十一月的倫敦電影節等各國展映。但由於此二作日後討論度較低,這段期間普遍被視為他在《戀戀風塵》(1986)與《悲情城市》(1989)兩者間的低潮或儲備,或不全然屬實。
而在《一切為明天》的前後的國外旅程中,其中一站特別引起了爭議:根據《中國時報》與《華僑日報》的報導,侯孝賢於六月二十二日赴香港出席了一場「影藝戲院」的媒體招待會,為《尼羅河女兒》作為戲院七月初開幕的首映造勢。但該戲院的投資者「銀都機構」,是一九五○年代中國影人赴港創辦的「長鳳新」三家左派電影公司,於一九八二年的重新整合——此舉可謂挑動了兩岸分治與冷戰對立的敏感神經。在招待會上被媒體問及的侯孝賢回覆,台灣已開放大陸探親與轉口貿易,中國電影也在台上映,⓯除表述此行沒有顧慮,也透露登陸拍片的期待。

行政院新聞局隔天隨即嚴正聲明依法查辦,並以張毅一九八六年在香港創下票房佳績的《玉卿嫂》,於左派的普慶戲院上演,致出品的天下公司遭到撤銷許可登記為警例。出資《尼羅河女兒》的綜一唱片公司及侯孝賢除先後赴新聞局說明外,亦極力與受委任處理國際版權的香港影評人舒琪,在媒體上表達懸崖勒馬之心,惟因簽約認知落差與撤片時程太趕,未獲影藝戲院接受。本案八月初隨綜一再次強調正向香港政府申請「禁制令」、要求停演下落幕,後續是否有相關懲處不得知;到了九月十日,國防部突然宣布邀請侯孝賢拍攝MV宣揚軍威。雖無法證實兩件事之間的因果關聯,時間點接近不免引人聯想。不過,《尼羅河女兒》在明知規定下與香港方單行口頭協議、出事後雙邊來回斡旋等過程,幾乎與《玉卿嫂》的「疏忽」如出一轍,再加上侯孝賢在招待會上的侃侃而談,也令人猜想其是否真只是「誤」闖左道抑或為「轉口貿易」的一次嘗試。尤其,兩者的搭橋並非憑空而生,銀都機構旗下的南方影業在一九八四年所舉辦的「八十年代中國電影精選雙週」,即已促成勤在港台間觀摩兩岸三地電影新作的台灣新電影戰將,與中國影人在尖沙嘴香港大酒店密會。⓰
儘管《戡亂時期國片處理辦法》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廢止前,持續管制台灣電影產業,層出不窮的個案卻不斷挑戰著新聞局難服人的浮動標準,兩岸左右陣營的勢不兩立遂顯露縫隙。除了前述台灣電影的西進,同年香港導演許鞍華也曾為禁演四年的《傾城之戀》,訪台拜會新聞局與宋楚瑜等黨政人士,並在高調宣示為自由影人後,其登陸拍片後與審查港片在台上映資格的「港九區自由總會」間的多年纏鬥,才終暫告段落;而銀都機構同樣為顧及港片所高度仰賴的台灣市場,亦曾多次偷天換日地借其他獨立電影公司之名成功登台,並以隔年在屬右翼陣營的金馬獎上打敗《悲情城市》的《三個女人的故事》達至巔峰。
烏登曾指出,「如果侯僅僅依靠新電影的話,他的創作生涯可能已隨這場運動一起結束了。」而台灣電影作為「政治與經濟雷區」,在雙重夾殺下也不乏難以另闢蹊徑的犧牲品。⓱當我們重新梳理這段文化冷戰歷史,應可一窺侯孝賢等人在離開中影後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角力。尤其《尼》除了出口香港一事,在台上映前亦反覆與新聞局電檢處拉鋸,絕非如後來《一切為明天》表象呈顯的雙方合作無雙或單向聽命行事。而港台各種隱身、變色與輸誠之例,亦可提醒我們留意遊走其中複雜的政治判斷與權衡;另一方面,隨兩岸三地改革開放的大勢所趨,侯孝賢等人乃至香港電影,也逐漸為經濟上的資金與出口需求,不斷試探政治封鎖,進而摸索出不同於新電影時期的產業求生之道:借力使力地往前衝撞,如有碰壁則退一步協商角力;方成就《悲情城市》日後的一刀未剪及「侯孝賢經濟學」的預售版權模式。
「新電影之死」的「死」
曾參與《新電影之死》論戰的邵懿德,去年在臺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台灣.八○.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論壇上,為我們今天的重探點出關鍵提醒:《一切為明天》相較於現在的政治宣傳,根本是「小巫見大巫」。⓲而在書寫本文的當下,台灣正歷經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與共軍繞台軍演,而達抗中保台的激情高峰;我們當然需要批判《一切為明天》所反映之政治與資本對文化的穿透、收編與吞蝕,以及「冷戰/戒嚴/反共」所遺留至今的戰爭意識,歷史時空的轉變或弔詭的重複自身,卻也為藏品增添了論述位置在二元之外的複雜性。故本文嘗試在《新電影之死》的論述基礎上,還原暗藏在影像背後的「黨政軍權力鬥爭」與「文化冷戰」兩個未明的昨日軌跡與相應的物質基礎,為日後的重訪提供線索。
在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初,台灣隨著政經結構與治理模式的轉型而「死去」的新文化運動,其實不只新電影或爾後的「另一種電影」;王墨林在一九九○年即曾宣判自己曾投身的「小劇場已死」。⓳雖然在時序上以及與體制的關係等層面大相徑庭,卻皆在賜死之餘,嘗試將「死」解構出政治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再現。換言之,藏品本身的重見天日可能無助於記憶的重建或歷史的釐清,唯有對應回作品與論述所發生的「社會」,探究其之於創作者與評論者的意義,否則《新電影之死》的「腹語」,也終將使其從一場後設批判的「運動」,淪為缺乏歷史意識的意識形態「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