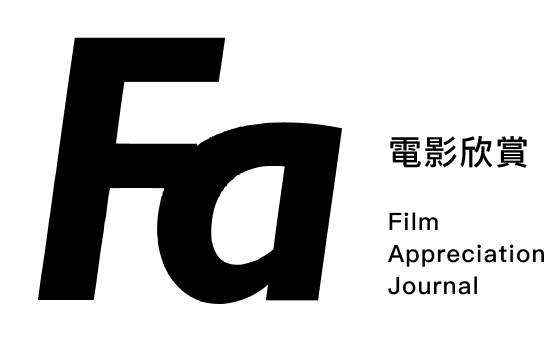誰的新電影,誰需要新電影?

誰的新電影,誰需要新電影?
人們的行為在世界歷史中造就不同於他們本身意志所要實現的東西,而這類東西卻是本質性的。人們雖然在完成各個目的,但達到的結果卻是「內部的東西」,儘管這個東西不在他們的意識和目的中。黑格爾做了這樣一個說明:某人想用燒房子的方法報復另一個人,但他的行為卻會超出原來的目的,例如會燒毀整個村莊而殃及眾人,最後反倒使肇事者受到懲罰,而這些都不在他的本意中。
——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布克哈特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態度〉
無法得見的新電影與文化公共領域
《未來的光陰:給台灣新電影四十年的備忘錄》(林松輝、孫松榮主編,2022)在企劃編輯的過程中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我們希望將書中篇章提及的重要作品,以圖錄年表的方式呈現在卷首。然而,儘管當年由中央電影公司(下稱中影)出品的作品,相關權利在二○二一年中影與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和解後,轉移給黨產會代管,而讓我們至少還能使用;卻也仍有為數不少的作品,不是無法找到權利人,就是權利人能夠提供的圖像畫質太差而婉拒了我們的授權請求。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免意識到,這種許多作品無法得見(許多中影本已修復完成上架網路平台的作品,也因權利轉移而暫時在平台上消失)的景況,大概也正是「台灣新電影四十年」此刻的歷史寫照,於是便在圖錄年表中,為這些作品放上了標註著「無法取得授權」與「無法取得清晰圖像授權」的電視雜訊圖像。

這種無法得見或許會讓人聯想到《超級大國民》(萬仁,1994)中的「獅子林——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以及來來大飯店——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在一九九三年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區首次被發現的那個時代,這些地點都還沒有今日已然為人所知的「不義遺址」稱號。而在當時正歡欣鼓舞走向民主化的台灣社會中,政治姿態顯得寂寥冷清的這部電影成為一種預見——那些在時間中迅速被掩蓋的地景,會在二○一五年電影被數位修復、台灣青年世代在嶄新的集體政治動力催迫下產生對本土歷史巨大熱情的時刻,以一種沒有形體的記憶形式現身在各種討論的話語中。這可能正是台灣新電影運動與其創作集團後續作品最有趣的雙面性:他們一方面對於外在的政治與社會情境給予超前時代而未必自知的預視,一方面也因為這種超前,而讓解嚴前後文化公共領域尚未浮現的台灣社會難以給出足以回應他們的社會論述。而一直要到我們身處的,電影機構逐漸成形的數位修復時代,我們才開始慢慢從得見的作品一方面重新看見,一方面醒覺原來還有如此多未見。
近年來,在有志之士的努力與相關檔案的開放下,「電檢史」至少在電影研究領域中開始成為一個題目,而且也被放進匡正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的轉型正義架構下來審視。這也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即使一九八三年立法的《電影法》保留了被廢止的《電影檢查法》中的電檢相關條文,讓《電影法》仍舊是以管制為核心精神的法律,但在現今主流的台灣電影史敘事當中,《電影法》立法依然時常被陳述為「開明派」新聞局長宋楚瑜肯定電影事業是「文化事業」、並賦予政府獎勵與輔導責任(《電影法》第39條),❶ 進而推動電影製作走向「寫實」與「貼近生活」,來回應輿論對於國片的批判,各種政策作為中介的一個重要面向。❷ 這種「宋楚瑜推動台灣電影走向專業化、國際化、藝術化」的敘事,經由新聞局下屬的對外文宣刊物《自由中國評論》月刊(今《台灣評論》月刊)和《光華畫報》(今《台灣光華雜誌》)進入國外學術視野,像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的《光華畫報》就詳實記錄了當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宋楚瑜如何儀式性地將金馬獎交付給代表「民間」的中華民國影劇協會理事長明驥(新聞局不再主辦),又如何因為讓電影「提升為文化事業」而受到「民間」肯定,從明驥和童月娟、白景瑞手上獲頒「特別獎」。❸這些今日看來令人感到樣板到有些發噱的場景,讓這個時期的台灣電影,特別是在中影體制內進行的電影產製在歷史敘述中有了相當程度的「國策」色彩。

在電影被「提升為文化事業」的同一時期,國民黨政府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1,下稱文建會)、訂定《文化資產保存法》(1982),延續著一九七○年代嬰兒潮世代青年尋根熱潮,開始進行「發揚中華文化」的文化政策工作。而開始被視為「文化事業」的電影,似乎也有了相應的政策作為:一九七九年,由片商公會建議運用外片進口繳納費用捐助成立的「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附設電影圖書館」(下稱電圖)成立。電圖如何在一九八○年代透過「金馬獎國際影片觀摩展」在台北建立「電影文化」,甚或藉由「金穗獎」將許多年輕創作者送進業界,已是為我們熟知的故事;然而,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儘管在主事者強力主導下,電圖成為了以「電影保存」為核心任務且脫離電影基金會獨立的「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但組織長年並未立法,也凸顯了電影機構多半以個人意志帶動工作,而始終未有政府整體政策領導的困境。換句話說,從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電影產業、電影政策(管制)、電影文化、文化政策始終維持分立,政治的民主化並未塑造出屬於電影的文化公共領域。
「寫實」的「電影民主化」精神?
另一方面,「國策」色彩在侯孝賢、楊德昌(下稱侯楊)兩位新電影代表性導演的作品不斷入選國際影展的情境下被逐步強化,也讓(其實只有指向侯楊作品的)「新電影在各類國際影展屢獲肯定,打破外交藩籬,成為宣傳台灣形象最有力的媒介」❹這類論述漸成主流。這類論述暗示「具有國際聲望的卓越藝術作者」(侯楊)與「以在地市場為主而較不具獨特作者風格的二線導演」(其他人)的區分,和前述的「《電影法》肯定論」一致,忽略了此時台灣電影創作者與體制(無論政治或市場)周旋的能動性,以及他們作品中潛藏的各種社會與民主意識。事實上,第一位將新電影介紹到法國的影評人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在論述新電影時,談的就是與法國新浪潮類似的「電影民主化」精神,亦即讓觀眾「第一次看見福爾摩沙自然」。❺但在台灣島內,「寫實」作為民主表現形式的論述在一九八○年代尚未生成,反而被視作國家反省電影政策的產物,也讓「寫實」這個理應能夠觸發電影社會論述潛能的形式,逐漸被窄化到作者美學的討論上。

舉例來說,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不難在《看海的日子》(王童,1983)裡發現,此前台灣電影中少見的漁村生活紀實描繪(也就是阿薩亞斯口中的「第一次看見福爾摩沙自然」),女性獨力生養孩子的故事更對性別意識已經全然相異的今時充滿預視。但在一九八○年代的現實情境中,儘管《看海的日子》是陸小芬從脫星轉型,進而拿下金馬影后的作品,對評論圈而言,卻也只是因著主角、情節而成功大賣的話題之作。當代的我們不難在一九八○年代(不僅止於新電影)的台灣電影裡,從地景、性別、兒少、族群到各種社會議題與歷史重述,重新閱讀出推動當時台灣成功走向民主化的重要集體動力——新富社會裡積極追求自由的中產階級意識。但在當下的政治與市場結構中,藝術與否、商業與否成為比較迫切的問題,也就自然讓多數評論者已經指出其虛妄的藝術與商業之辯成為電影論述核心。隨著侯楊在國際上成為台灣電影藝術的代表並逐漸進入國際學術視野,我們反而欠缺足以談論其他電影作者的語言。
新電影二十年時,這種論述的「去時空化」缺失已經被指出,❻但至今也沒有太多改變,而且隨著作品湮沒日遠,我們愈發難以重新發現一九八○年代台灣電影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其時,民進黨首度執政,即使身處國會少數,仍然勉力推動台灣文學與歷史的學術建制化工作,成立不需立法院三讀通過「組織法」的四級機構台灣文學館和台灣歷史博物館;相對來說,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儘管迭有將電影資料館升格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或在新莊興建「國家電影文化中心」之議,最後也沒有太多進展。相較於文學和歷史的文化主體意涵,以及領域中有許多過去就和黨外運動密切連結、甚至並肩作戰的創作者與學者可以進行積極的政策建議,因為生產結構而一直帶有「國策」色彩的台灣電影,欠缺建制化的政治條件,唯一曾經以民間之力形塑台灣電影產業的台語片,儘管歷經一九九○年代電影資料館的搶救工作,也未曾在文化菁英視野中取得論述位置。❼文化機構和學術建制的雙重欠缺,讓台灣電影文本即使深具社會論述潛能也不容易開展,特別是電影媒介在物質和市場結構上的特性,都讓舊作重新流通的可能性遠低於文學。當新電影逐漸成為無法得見的「傳說」,新電影的敘事也就更加趨於單一。

電影進入數位時代提供了新的契機:新聞局和文建會整併成「文化部」的第一個完整年度(2013),就獲得四年期、每年預算上限可達三千萬的科技發展計畫「台灣經典電影數位修復及加值利用計畫」。這筆預算從一開始就超過文化部(新聞局)例行捐助電影資料館預算的三分之二,也讓電影資料館(隨後升格更名為「國家電影中心」)開始透過修復作品建立新的社會溝通介面。如同前述,數位修復版的《超級大國民》具現化了當代觀眾仍然幾近空白的白色恐怖歷史想像;尤有甚者,一九九○年代的街頭民主與黑金政治場景也被重新看見。這些重見,在在讓《超級大國民》宛如重生為一部二○一五年的電影作品,複視兩段重要的歷史時光。於是,當預算和人力有限,並非所有作品都能走到數位修復時,由於修復作品畢竟會比單純保存者獲得更高的曝光,「修復什麼作品」、「什麼修復作品可以被看見」(權利問題)、「在修復作品中看見什麼」,這些提問也就讓電影社會論述的重建成為可能——我們在電影中看見的,其實是今時此刻我們自己的愛憎。
電影保存修復的歷史重述
在本具文化公共領域的社會,電影的保存與修復是相應的社會論述不斷積累的過程;而在歷史持續被迫中斷(電影史亦然)的台灣,電影保存與修復則逐漸成為一種歷史重述工作,一邊為電影史的各種空缺、補遺,一邊發現許多湮沒的歷史小徑。這種重述工作在晚近台灣文化生產中值得作為參照的或許是賴香吟和朱嘉漢的小說書寫:因為歷史和我們之間的間隔如此明確,小說家似乎不是試圖置身在歷史人物的時空刻劃他們的行動,而是在我們的時空想像他們如何行動,彷彿時間到了他們那邊戛然而止,而在不知道什麼地方重新開始才來到我們這裡。已經活在歷史人物與電影文本的未來中的我們擁有特權,能夠不囿限於歷史時空當下的論述焦點來進行討論。

舉例來說, 在藝術與商業之辯未休的一九八七年,《惜別海岸》是萬仁叩關商業體制的失敗之作,❽ 或是終結了台灣新電影的那顆子彈。❾ 但到了現在,我們卻可以一方面縱向地,從《惜別海岸》、《超級大國民》到《超級公民》(1998),重新發現萬仁在台灣經濟與政治最狂飆的時代,如何一以貫之地讓被排斥到社會邊緣的人,在充滿歷史殘跡的台灣地景中遊走與尋求救贖;另一方面橫向地,從情節與手法類似《惜別海岸》的日本新浪潮電影《略稱:連續射殺魔》(A.K.A. Serial Killer,足立正生,1969)和《赤貧的十九歲》(Live Today, Die Tomorrow!,新藤兼人,1970)(兩部作品皆改編自一九六八年的永山則夫連續殺人案)發現,在新電影的寫實基底之中,讓看似完好無瑕的城鄉環境出現各種破口的「風景論」,可以成為閱讀萬仁繁複政治思考的一種取徑。
或者,在一九八三年,《大輪迴》(胡金銓、李行、白景瑞)是被《兒子的大玩偶》(侯孝賢、曾壯祥、萬仁)「擊敗」的「舊世代導演」作品,「標記台灣電影的新舊世代交替」❿,《搭錯車》(虞戡平)則是香港商業體制進軍台灣造就的票房巨作,兩部戲劇張力強勁的電影都像是新電影的「反面」;但如今看來,《大輪迴》由白景瑞所執導的第三段和《搭錯車》裡由林麗珍領軍的舞蹈演出,其實共同記載了台灣現代舞再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的時刻,舞者在城市與偏鄉地景中現身的姿態,成為台灣文化史書寫重要的材料。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輪迴》非但現代,而且足以象徵古典的大陸詩學如何在時代遞移中在海島「靈根自植」。

又或者,我們藉由源出新儒大家唐君毅的「靈根自植」,把眼光拉得更遠一點,看向根本不是台灣電影的《愛在他鄉的季節》(羅卓瑤,1990)裡出現了什麼台灣:《大輪迴》中不難令人聯想到雲門舞集,在演出描繪先民渡海來台故事的《薪傳》(林懷民,1978)時,將陳達請到現場演唱的《思想起》——「台灣後來好所在,經過三百年後昭昭知」⓫;或者「博士論文一直沒寫完,所以一直留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強烈指涉的「黑名單」。一九九○年入圍八項金馬獎的《愛在他鄉的季節》是台灣觀眾同悲六四的一種媒介,如今卻為我們揭示,台灣(與台灣電影)可能是同時容納中國人、香港人與台灣人離散之情的最後一個「三百年後好所在」。
事實上,胡金銓、李行和白景瑞拍《大輪迴》時也不過五十出頭歲,實在談不上「老」。他們在一九八○年代後的快速消逝,只是台灣社會在這個時期隨民主化而來的各種劇烈典範轉移的一個側面。而且這個強烈的加速度,讓新電影在還來不及(也欠缺足夠的客觀條件)取得社會基礎時,就以更快的速度在歷史中消退。因應不斷出現的外來政權覆蓋而生長出自我抹消歷史傾向的台灣社會,這四十年來面對的是更加巨大的世代割裂感。然而,在這個電影產業、電影政策、電影文化、文化政策初步開始匯流的時刻,我們似乎看到機會的窗口,能夠透過重新觀看新電影、不是新電影的台灣電影、不是台灣電影的華語電影,去發現於今日猶不過時的民主與自由徵兆。
更有甚者,《桂花巷》(陳坤厚,1987)台語聲片重見天日的故事⓬不僅為我們揭示了,我們以為自己看見過的,或許並不曾真正看見的(《桂花巷》在《未來的光陰:給台灣新電影四十年的備忘錄》的圖錄中,同樣是「無法取得授權」);也提醒我們,「《電影法》肯定論」和「蔣經國推動民主」同樣是來自威權統治者視角的國際政宣辭令。當我們已經不陌生於一個世代台灣人如何抵抗進而推倒威權的故事時,也不要忘記,一九八○年代的台灣電影正是這些人身影的載體。這或許才是內含大量新電影作品的中影資產,在四十年的此刻被黨產會移交給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管用的最大意義:讓新電影對自由的追求能被重新看見,是我們從「追求自由的民主」前往「追求正義的民主」最好的資糧,也正是阿薩亞斯在遙遠的一九八四年初見台灣新電影時,心旌為之動搖的「電影民主化」最好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