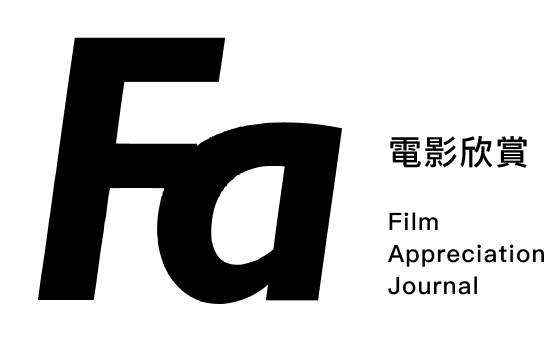從選片與放映出發,Arsenal柏林兵工廠的非典型之路

從選片與放映出發,Arsenal柏林兵工廠的非典型之路
即將於二○二三年邁入一甲子的「兵工廠——電影及錄像藝術協會」(Arsenal - Institute forFilm and Video Art)從舉辦獨立電影放映起家,策劃影展、典藏電影、建立數位化資料庫、推動影像教育,機構和其創辦人格雷戈爾夫妻(Erika & Ulrich Gregor),可以說是形塑一整個世代以柏林為中心的影迷認識世界電影的關鍵核心,也是許多電影人在創作上獲得認可與動力的地方。
兵工廠不同於典型的電影資料庫/博物館那般依循特定的典藏與研究範圍,來建構機構的定位與認同,例如國家型的電影中心多是以建立其國族或區域電影史為己任,或者擁有一批特別的實驗電影典藏作為機構特色。類似兵工廠這樣以選片、放映為主導,重新組織並建立影片脈絡,以補充並重構大眾對電影史之認識,進而進行典藏的機構,在影像檔案機構的例子中是相對少見的。
今年年初,關於格雷戈爾夫妻和兵工廠的紀錄片《Come With Me to the Cinema–The Gregors》在柏林影展論壇單元(Forum)首映,年近九十的兩老精神抖擻地出席在論壇單元主場地德爾菲電影宮(Delphi-Filmpalast)的放映活動,一如外界所知,這對夫妻結褵超過半世紀,幾乎沒有一天沒有電影,即便他們從兵工廠退休後,仍勤勞地參與各地影展,肩並肩坐在影廳,以一天只吃早餐一餐的飢餓狀態吸收著眼前銀幕投射的光影。❶疫情期間電影院關閉的時候,他們依然在家一片片VCD、DVD,甚至是VHS不停地看;他們不只是看,還熱烈討論。對格雷戈爾夫妻而言,電影能被觀看,能被談論,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這樣的理念,六十年來未曾動搖。

一九六三年,德國國家電影中心(Deutsche Kinemathek)剛剛成立,年輕的格雷戈爾夫妻即創辦獨立電影團體「德國電影中心之友」(Freunde der Deutschen Kinemathek),此為兵工廠的前身,舉辦獨立電影放映,以提出與官方機構強調保存國家影音經典的另一種電影組織路徑,而當時這樣強調選片、放映的運作方式並不被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FIAF)認可為「電影資料館」(archive)。
「德國電影中心之友」成立初始帶有抗拒、反官方機構作風的「叛逆」性質,他們在過度傾向好萊塢電影、國族主義式電影的柏林影展期間,舉辦「青年電影週」(Woche des JungenFilms),讓那些不可能出現在當時影展主競賽的古巴電影、東亞電影、尚未知名的新銳導演,如法斯賓達,得以有機會被看見。一九六○年代末正是學運浪潮席捲歐洲的時代轉捩點,西德、法國、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精英、反威權等抗議活動興起——一九六八年坎城影展經歷「抗議右翼勢力」事件後,隔年影展創立平行單元「導演雙週」(Quinzaine des Réalisateurs)選映具批判視野、不被主競賽選入的電影。而這股世代覺醒的浪潮,亦為柏林影展的改革埋下了種子。
一九七○年第二○屆柏林影展發生「反戰電影《O.K.》撤片事件」❷,引發群眾抗議影展威脅創作自由。這場風波進而促使保守的官方單位做出改變,先前早有批評指出柏林影展過於注重明星光環、一昧吹捧好萊塢電影,呼籲改革的聲浪已經醞釀多時。此次風波後,柏林影展委託格雷戈爾夫妻規劃一個放映更多元開放、具批判性的電影單元,於是首屆「論壇單元」於一九七一年正式成立,從不滿柏林影展的獨立放映活動「青年電影週」,變成開拓柏林影展電影光譜的單元。
格雷戈爾夫妻運作電影組織並不是想與官方敵對或競爭資源,他們名副其實地是「德國電影中心之友」,扮演著補充官方機構不足的角色。❸「論壇單元」選映蘇聯導演、共產國家、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品,除了劇情長片以外,也放映紀錄片、實驗電影和短片,更重要的是,格雷戈爾夫妻不把電影放映視為只是放電影而已,他們相當看重對電影的討論,因此「論壇單元」一定會伴隨著相當扎實、豐富的映後討論,而通常是由當時在電視台擔任電影評論家的格雷戈爾先生負責主持,諸如貝拉塔爾、北野武、阿巴斯.奇亞洛斯塔米、賈樟柯、王兵、王家衛都曾經是座上賓。

除了影展期間的放映以外,格雷戈爾夫妻也策劃全年度的節目,對他們來說,電影不應只是單純地視為「一件藝術品」,而該是各種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美學的、反美學的因素都能在其中找到對話的可能,也因此兵工廠放映電影不只是為了呈現藝術作品,而更是透過放映的過程,讓作品和創作者被大眾看見,在個體與集體、在電影與電影、單部電影與整檔節目之間產生脈絡與意義,是知識與文化生產的過程。無論是早年在市區的舊空間,或是現在在波茨坦廣場索尼中心的兩間放映廳,兵工廠都是熱愛電影之人聚集據點,是人們吸收最前沿的電影知識、交換想法的重要堡壘。
以選片、放映展開知識與文化意義生產之餘,兵工廠也典藏電影,但他們典藏的出發點並不是因為那些作品是影史的正典,而是那些作品是好電影,值得被觀眾看見並討論。通常被格雷戈爾夫妻發掘來的電影與創作者還處在沒沒無聞的階段,他們需要資金繼續創作與生活,因此買下他們的電影拷貝、邀請他們來放映作品,成了格雷戈爾夫妻支持創作者最直接的方式。
經過六十年的積累,兵工廠已有超過一萬筆的電影典藏,除了保存電影以外,他們也數位化、修復、建立資料庫、出版、發行與展映,讓電影得以繼續透過不同形式被觀看與討論。兵工廠目前擁有兩間實體影廳:Arsenal 1與2,還有Arsenal 3是二○二○年於疫情期間成立的線上放映廳;負責於柏林影展期間策劃兩個單元:論壇單元,以及強調擴延電影、在白盒子空間展映動態影像的「論壇延展」(Forum Expanded)。此外,兵工廠也積極推動影像教育與研究工作,建立起德國國內兒童與青少年影像教育的學習網絡,並邀請國際的研究者、策展人運用其資料庫進行相關研究與節目策劃。
二○一一年,兵工廠在德國聯邦文化基金會(The Federal Cultural Foundation)和德國彩券基金會(Stiftung Deutsche Klassenlotterie)的支持下,發起「Living Archive Project」活化電影檔案計畫,這是一個以策展和藝術創作為實踐方法的三年期計畫,邀請策展人、學者及不同領域的創作者,包括當代藝術、電影、表演藝術、音樂等,自由觀看並使用兵工廠典藏的影音檔案,舉辦放映、工作坊等活動,最終以實體展覽、專書出版品與線上資料庫的方式呈現成果。
此計畫對兵工廠後續十年的經營方向極具指標性,無疑也對外宣告這個帶有「反傳統電影資料館」基因的機構,正積極地奠基在透過選片、舉辦放映、策劃影展節目而積累的電影資料庫,重新思考電影保存與展映的關係,當代電影機構/資料庫面對影音檔案時的角色與任務。

特別是經歷數位轉向的此刻,科技的變革對電影拍攝、典藏與檔案化、策展與展映方式帶來巨大改變,同時也改變我們如何接收電影帶來的觀影經驗,確實是需要新的策略來面對電影機構的當代樣貌,反思數位化時代下「電影保存」的意義。當保存的不再是物質性的膠卷拷貝、文件,而是各式檔案(digital files)時,數位時代下的電影保存其實是無止盡的檔案管理工作。電影資料館/機構的角色作為傳統的「守門人」(gatekeeper)已不足夠,而必須要是能運用檔案、在當代創作新意義的「策展人」(curator)。
正如同兵工廠在其機構宗旨裡標註的:「資料館(archive)是一個可以進行研究、策劃並生產新事物的空間。」電影資料館/機構不再只是保存電影、守護影音文化資產的地方,而更是個能轉換、擴展,並得以從中汲取並形塑集體記憶的影音檔案寶庫,它作為一種展示歷史與文化的獨特傳播方式,提供途徑讓我們得以想像並凝聚社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