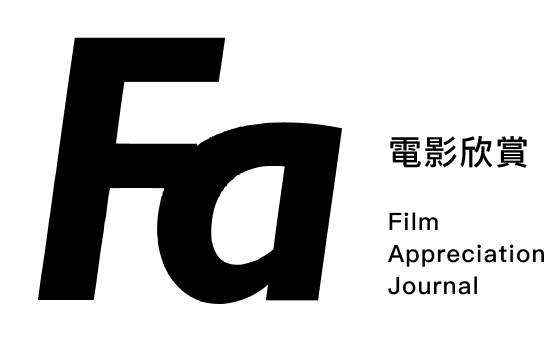以一張雜誌照片,追問檔案的敘事邏輯與意識形態──總結並終結高達毛派時期的《給珍的信》

以一張雜誌照片,追問檔案的敘事邏輯與意識形態──總結並終結高達毛派時期的《給珍的信》
《給珍的信》Letter to Jane│尚盧.高達、尚皮耶.戈罕Jean-Luc Godard, Jean-Pierre Gorein│法國│1972│52min
一九七二年越戰期間,美國影星珍.芳達造訪北越河內,留下許多影像紀錄,引來美國保守派人士大肆抨擊叛國。照片在法國媒體刊出後,導演高達與戈罕以其中一張照片為題寫了一封信,透過兩人來回朗讀信件內容的方式,一步步解構這張新聞照片的意義。此次放映為高達之經典作品首次在台曝光。
紀錄片《給珍的信》(Lettre à Jane / Letter to Jane)可說為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一個創作轉折與危機的分水嶺。自從六八學運,高達放棄國際知名導演身分,與年輕激進學生成立「維托夫小組」(Groupe Dziga Vertov),社團名稱是為了紀念蘇聯先鋒導演維托夫,目的為擺脫作者光環,以集體創作之姿,服膺風靡巴黎知識圈的《毛語錄》,拍攝多部極端左派政治電影;此時期作者導演高達與年輕學生尚皮耶.戈罕(Jean-Pierre Gorin)聯合執導,一九七二年兩人不但共同拍攝劇情片《一切安好》(Tout va bien),同年更一起執導紀錄片《給珍的信》;前者為「維托夫小組」最高成本也最為著名的電影,後者則為壓倒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的最後一部作品,自此兩人分裂、團體解散。「維托夫小組」於六八學運後的大起大落,一般被稱為高達的「毛派時期」(les années Mao)。
如紀錄片本身旁白不斷提到,談到《給珍的信》,必須談到《一切安好》。身處「後六八學運」時期,「維托夫小組」於拍攝多部低成本政治影片後,亟欲開創新路線,此時高達找到願意冒險的新製片,異想天開欲於傳統片廠,拍攝一部高成本政治寓言電影,尤其特別請到珍.芳達(Jane Fonda)、尤.蒙頓(Yves Montand)兩位如日中天的美、法大明星主演,前者剛以《柳巷芳草》(Klute, 1971)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本身為著名的反戰人士,後者則演出政治電影《焦點新聞》(Z, 1969),為長期支持法共的演員。電影講述一對夫婦(珍.芳達飾演的美國記者和尤.蒙頓飾演的法國導演)如何深陷肉品加工廠的罷工風暴,進而檢視兩人知識份子身分於消費社會中的角色位置─情感疏離、剝削底層與被高層剝削。雖以兩大明星作為賣點引發媒體矚目,然而過於激進的極左內容與前衛的反好萊塢手法,不僅評論毀譽參半,大製作更以票房失敗收場,最後讓高達此後多年不碰明星與片廠。
此時越戰正酣,反戰立場鮮明的珍.芳達特別飛到北越,訪問被美軍轟炸的越南人民,並由越共拍照報導,製作全球宣傳,引爆美國指控其「叛國」的強大爭議。於法國方面,《快訊》週刊(L’Express)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刊登珍.芳達於北越的照片,不僅引發全國討論,高達更受到政治理念的衝擊與藝術概念的刺激,再次與導演搭檔戈罕合作,以超低成本五百元美金,❶自寫自錄旁白,拍攝《給珍的信》,整部五十二分鐘影片只聚焦於一張照片:《快訊》週刊所刊出的珍.芳達如何在北越聆聽人民受苦的見證。
經由一張看似平凡中立、甚至立意良善的雜誌照片,高達帶領「維托夫小組」檢視其代表的菁英敘事邏輯,背後的社會價值體系,最後不僅有意識於紀錄片中批判照片代表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更不自覺暴露影片本身製作的蘇維埃意識形態爭議,成為「維托夫小組」解體的最後絕響。
由一張雜誌照片出發,本文嘗試解析高達「維托夫小組」提出的菁英敘事批評、美學主義批評,與高達自身意識形態的自我崩潰與持續演變。
以「明星崇拜」製造「藝術商品化」
這張珍.芳達在北越的照片,看似中立客觀,表達一位美國人在「敵方」聆聽自己國家造成的惡行,不管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脈絡,都有可對照查證之可信度與真實性。然而,高達「維托夫小組」卻認為,這張照片是表達社經地位的「面具」,傳播新資本主義的「謊言」,表現的更是一個明星不斷強化消費社會的展演。
於這部《給珍的信》中,高達首先將珍作為一個他自己的女性朋友和珍.芳達作為一個電影明星,兩者劃分開來,他批評的對象主要是她的社會地位功能,而不是她作為女人本身(雖然高達和戈罕兩位導演完全承認自己的男性視角,卻留下空白,沒能力或沒意願進一步辯證)。接著,高達直接表示:「就像在《一切安好》,妳在電影中的明星地位,和這張照片是一模一樣。」這張照片主要意義,之所以造成強大影響力,正是因為她是個獲得奧斯卡獎的好萊塢明星,這也是為何整張照片只有珍.芳達的臉是美麗的四分之三側臉,對焦清楚可見,其他出現的越南人,不是背對鏡頭,臉被遮掉近一半或全部,就是沒有帶到焦距。
高達「維托夫小組」認為這張照片「導演」了主流社會認知場景,表現出珍.芳達無論如何都是最重要的焦點明星,讓看似無辜、偶然捕捉到的影像,再次成為資本主義宰制下的一個製造產品。這裡我們完全可以延伸對照閱讀,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L'OEuvre d'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bilité technique),提出二十世紀影像如何被「明星崇拜」(le culte de la vedette)宰制,即是「維持知名人物的魔力,一種縮減為商業價值的腐敗魅力」❷,不斷強化資本主義自身,因而「明星崇拜」影像之產生後果,即為「藝術商品化」(l' art comme marchandise),也就是說,不論是劇情片《一切安好》為了吸引票房,或是法國《快訊》週刊的照片是為了吸引讀者,珍.芳達都以美國好萊塢明星身分,鞏固新資本主義,將利益最大化。
高達「維托夫小組」指出,他們在這張照片最感興趣的,卻是背景失焦的無名越南人,他們是誰?他們為何在那?他們經歷什麼?希望什麼?若說這張靜照提問了「什麼是正常?」《快訊》週刊等主流媒體則以「明星吸引力」作為解答;然而高達觀看這張照片,認為其中最關鍵的,卻是「沒有任何人提到那些看似平凡的獨特事實」,也就是在珍.芳達身旁的那些無名、受苦、邊緣之人。
以「藝術政治化」對抗「政治美學化」
高達「維托夫小組」從電影與攝影的「明星崇拜」開始,再進一步追問消費社會宰制下的菁英語言、美學主義。在這張週刊照片中,珍.芳達與其說是展現一個聆聽他人的平凡女子形象,不如說表現出一種「好萊塢學派、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演技表演」。她不僅是個反戰份子,更是個美國明星,這兩種身分之融合,才於媒體產生意義。
高達更注意到:「取鏡並非無辜或中立。」由越共主導拍攝,由歐美媒體全球放送,這張照片似偶然捕捉珍.芳達看似聆聽的沉默姿態,卻精心策劃主流社會身分的權力展演,珍.芳達美麗的沉默,並非「捷克孩子面對大俄羅斯坦克之無語」,也不是「巴勒斯坦人腳踏國際組織造成爛泥的掙扎」。珍.芳達若有所思的影像「充滿了無意義」,傳達的是一個耀眼明星於陰黯場景,襯托對比之審美愉悅,明星在此呈現之美,是於北越鄉間戰場,展演菁英藝術遊戲的「不在場」(absenter)。
高達認為,「充滿無意義」之「不在場」,正是新資本主義的美學統治策略,珍.芳達於北越結合反戰份子與美國明星身分,是以美學遊戲強化了主流敘事的宰制,可說呼應班雅明所提出的「政治美學化」(esthétisation de l’art),班雅明將其定義為一種藝術的「負面神學」❸,即是在充滿混亂不純的現實當下,以一種不在場的「空無」,展現純粹自身永恆之美。珍.芳達以深入地獄場景的反戰姿態,不斷展演自身永恆的明星價值,成為一種消費社會崇拜的空無信仰。
高達「維托夫小組」提出,不管在週刊照片還是與他們拍攝的劇情片《一切安好》,都不斷在追問一個問題:「知識份子的位置在哪?」也就是菁英階層「於革命掙扎中,位置為何?」高達在此表達他與珍.芳達之差異,若後者將「政治美學化」,以社會議題作為背景,展演明星的永恆光芒,這位新浪潮導演則往相反方向走去,追尋班雅明所提出的「藝術政治化」(politisation de l’art),以混沌複雜的他者真實,質問自認永恆的菁英藝術本身。
高達認為「沒有清晰顯明的真理,而有晦澀陰暗的真理」;真實是什麼?不在於菁英語言想像的永恆秩序,而是面對渾沌真實的一種不斷藝術追問。於是,高達面對這張週刊照片持續追問,「誰在拍攝?為了誰?針對誰?」(Joué par qui ? Pour qui? Contre qui ?)高達於這張照片的取鏡手法、生成脈絡,看到的是發動戰爭的美國英雄主義,永遠位於視覺焦點,而無名的越南人民,則永遠在失焦背景,以至於高達在這部紀錄片中,提出了藝術辯證:「雜誌以照片說謊」。
「馬、列、毛意識形態」自爆與質變
若說高達「維托夫小組」於《給珍的信》有意識批判珍.芳達明星價值的美國意識形態,卻也無意識碰觸到自身飽受爭議的蘇維埃意識形態,兩種意識形態的相撞,體現在與珍.芳達的決裂,和「維托夫小組」本身之解體。
高達於《給珍的信》自覺需要避免自說自話,不斷提出與當事人珍.芳達的辯論挑戰,卻遭到後者斷然拒絕。早於《一切安好》之拍攝過程,兩人已立場不同,發生齟齬。此電影計畫找珍.芳達主演,似為票房考量,然而預算規模仍無法請到這位甫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明星。最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珍.芳達與製片達成協議,將無酬演出這部極左社會議題電影,只拿票房盈餘分紅。然在前製時期,高達卻發生嚴重車禍,住院達數月,電影計畫或被取消的風聲甚囂塵上,然珍.芳達堅持演出,才讓電影拍板定案。於片廠拍攝時期,高達因正在重傷復原,多為另一導演戈罕統整拍片、發號施令,高達若到片廠,脾氣經常變得十分暴躁,喜歡針對兩位大明星,珍.芳達與尤.蒙頓,專挑麻煩,讓兩大明星甚至於報章訪談公開抱怨;整個片廠氣氛之專制獨裁、劍拔弩張,由今天的觀點來看,可說為「有毒」(toxique)的工作環境。電影於一九七二年初拍攝,四月即於法國上映,票房慘遭滑鐵盧,以致珍.芳達最後並沒拿到酬勞。同年七月底《快訊》週刊刊登珍.芳達於北越之照片,讓高達大為震驚,即刻與導演搭檔戈罕製作《給珍的信》,隨即於十月在珍.芳達家鄉,美國紐約影展做世界首映。高達自述,他雖在《給珍的信》提出與珍.芳達公開辯論,後者聽到的反應卻非常直接:「你是笨蛋,你是大男人,你是混帳,尤其我還無償為你工作……」❹兩人關係自此決裂。
若說珍.芳達企圖對《給珍的信》做出回應,可能在於一九七四年的紀錄片《介紹給敵人》(Introduction to the Enemy,由Haskell Wexler執導)。片中記錄珍.芳達和其先生如何深入北越訪談,討論戰爭的影響、轟炸的影響與生活的狀態。此紀錄片於美國引起軒然大波,讓女星一生都在面對某些越南老兵或政治團體「叛國」的指控,可說珍.芳達持續以自己的女演員認同,介入反戰運動,並承擔後果。
《給珍的信》除了引發與珍.芳達的決裂,更成為「維托夫小組」解體前的最後一部作品。首先,高達與戈罕兩人導演搭檔已經走到盡頭,後者尤其對《一切安好》大多是其執行導演(因高達車禍受傷),宣傳時高達卻搶盡風頭、獨佔發言權,深感挫折;兩人合作《給珍的信》又是相同狀態,於美國宣傳時,戈罕直說,他們兩人合作形影不離,像是同志關係,然而他總是扮演沒有聲音的被動角色。後來戈罕得到補助,獨自拍攝第一部長片,高達卻在資金短缺時不予支持,終讓片子流產,兩人自此決裂,戈罕於是憤而流浪他鄉(最後落腳美國,擔任電影教授)。
除了個人關係,「維托夫小組」解散原因更應為意識形態危機。六八學運後,蘇維埃意識形態於巴黎年輕激進知識份子圈大行其道,成為「維托夫小組」成立宗旨,即為效法蘇聯先鋒導演維托夫之實驗精神。例如我們可以見證《給珍的信》如何信手拈來,隨時引用列寧思想、毛澤東語錄。然而,時至一九七二年,極左抗爭早已展現多年運動疲乏,蘇維埃之教條思想更顯過時,尤其《一切安好》之評論與票房慘敗,《給珍的信》更是成為「維托夫小組」解散的最後一根稻草,成員不僅開始分崩離析,尤其信仰不斷鬆動,連高達本人似也開始對列寧思想、毛主義懷疑,不久後團體終是解體。
然而,高達電影難道只是馬列意識形態掛帥嗎?法國美學思想家迪迪—裕柏曼(Georges Didi-Huberman)於《引用過去的高達》(Passé cités par JLG)一書研究指出,高達電影的思想發展,與其說以蘇維埃意識形態作為核心教條,不如說永遠共振本文提及的班雅明「藝術政治化」,其極左實踐與其說奉《毛語錄》為圭臬,不如說與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電影詩學」不斷互補,「高達與帕索里尼,宛如相反的兄弟,兩極相對,產生巨大的能量,由歷史連在一起」❺。
從信奉「馬、列、毛」到徹底崩潰,高達長達六十年電影實踐軌跡,其實更與班雅明「歷史天使」及帕索里尼「底層倖存」不斷對話。《給珍的信》雖代表高達「毛派時期」的結束,卻讓高達更自由探詢人類精神的「歷史天使」,如其八○年代以《萬福瑪利亞》(Je vous salue, Marie, 1985)衝撞無神與信仰,九○年代以《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 1989-1998)辯證精神與影像,二十一世紀更於其最新長片——《影像之書》(Le Livre d'image, 2018),探討人類如何面對戰爭災難的彌賽亞歷史。《給珍的信》尤其一直延續與班雅明、帕索里尼的思想連結,除了淋漓發揮班雅明「明星崇拜」影像批評之外,高達更以凝視照片檔案中,背景無名失焦的越南人,對話帕索里尼底層「倖存微光」(survivance des lucioles),以批判主流宰制的明星敘事,想像一種以平等邏輯,取代菁英邏輯的另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