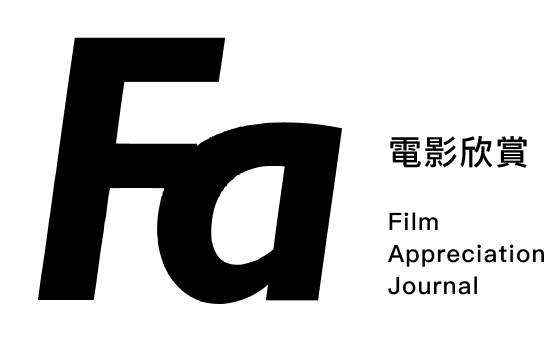製片廠裡長大的導演

製片廠裡長大的導演
「以前,想拍台灣故事,永遠沒地方拍。」二○二二年深秋,陪王童導演錄完金馬獎終身成就獎得主賴成英的訪談影片後,他急著趕往魏德聖導演工作室,要為魏導的新片提供美術協力,「我們兩個人很像,都想拍台灣故事,也都為找不到合適場景傷腦筋……。」
那一天,我頭一次聽到他盛讚台南岸內影視基地:「那時想拍早期台灣故事,永遠都只能到九份取景,拍到沒新意了,而且九份已經全變了。」面積達三萬餘坪的台南岸內影視基地在美術設計師黃美清的規畫下,已經打造出有日本大正、昭和時代仿古風情的街景建築,「還有大街、小街和民俗街,甚至還有火車站,只要微調改動,它可以是舊日嘉義、台南,也可以是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電影是國家文化的表徵,中影民營化之後,台灣就不再有大製片廠了。那時候的我們既有復古街坊建築,也有大棚搭景,像是大海裡的魚,可以到處遨遊,現在的電影人則像是精緻池塘裡的魚,視野和能耐都不一樣了。」提起製片廠,王童的眼中有火焰,亦有唏噓。
一九八四年初夏,走訪位於士林外雙溪的中影製片廠,首次見到王童導演,也見到了搭在攝影棚內的《策馬入林》場景。
棚內有座仿唐風情的廢棄廟宇,破舊建材在微弱光影照射下有一種斑駁陰森感。廟旁是馬廄,對面有個池溏,林木之間還有斜躺著幾尊仿雲崗石佛的雕像,現場滿是灰塵,池塘邊的石頭有泥有土,一時片刻不知如何蹲坐,王導看見我滿臉疑惑,直接開示:「我把電影的時間背景設定在五胡亂華年代,那是民族大遷徙的年代,受到政治或軍事的影響,也有饑荒元素,困於生計,很多民眾淪落成了盜匪。」戰亂滄桑,卻都是烏合之眾,難怪人人衣衫襤褸,不美觀,卻呼應著時代,也符合了劇情質感。

「分鏡時,我都先想好了攝影機位置,搭景時就先預留好攝影機需要的空間,也想好了光的來源。」王童強調攝影棚內作業講究的是「人工製造」,棚內光影要與外景連接呼應,開拍前他會帶攝影師和羅盤逐一看過外景地,確認日出日落光影角度,進棚時就知道該如何要求光影,他走到窗櫺前告訴我:「女主角彈珠被盜匪擄走,丟進匪窩裡,第二天天亮時,她從雜草堆上抬起頭,有光束透過窗櫺照了進來,現場還要放煙,製造清晨水氣霧境,光是這場光影就足足打了一天,才達到我的要求,那種精細龜毛程度幾乎是現在的工作者難以想像的。正因為難度高,所以那時侯孝賢和楊德昌都來探班,研究我怎麼用這麼少的錢搭出這麼實用的景片,那是台灣電影史上已經消逝的棚內製作技術,只可惜拍完《策馬入林》後,那個攝影棚就拆了,改做遊樂場去了。」是的,兩、三年後,遊樂場進來了,漢堡王也來了,中影拍片基地成了賺錢的金雞母,留給拍片的空間日益緊縮。
一九九八年仲夏,再在中影製片廠見到王童導演,他已經從美工升做製片廠廠長,然而電影不景氣,拍一部賠一部,少見劇組搶景拍片,遊客量也急劇萎縮——中影文化城不復昔日車水馬龍盛況,然而有線電影崛興,攝影棚紛紛轉租給電視台做綜藝棚去了,再見到王童時,他風塵僕僕去拜會電視台老闆,打躬作揖,祈求新一年合約順利,租金滾滾,閒談中總是哀聲歎氣:「老闆只想坐著收錢,不敢再冒然拍片。」

提起片廠興衰,沒人比他感慨更深,一九七○年代初期,中影文化城舊址原本是萬坪空地與廢墟,當時廠長明驥想搭個場景可供武俠片使用,王童建議先搭個酒樓,「當年預算只有六萬五千元,我們只得到北投、三重和辛亥路等拆舊屋材料行,用最便宜價格買下堪用的舊木料和磚瓦來蓋,結果我們還替公司省了六千元。」除了省錢,這間酒樓完工後三個月就因拍戲外租,替公司賺進了五十餘萬,於是明驥繼續要求王童和翁文煒陸續完成四合院,同時挖了護城河,沿著河岸蓋起城牆和城樓,陸續有了當舖、茶館、土地廟和王府等大小建築,最後還在護城河裡安排了一隻機械恐龍,三不五時帶著吼聲鑽出河面娛樂遊客,還完成了第一座水底攝影棚,除了可以用來拍戲,平常還可以當游泳池招徠會員,兼具拍片和觀光功能的中影文化城,在一九八○年代成為中南部觀光客包車遊覽的觀光景點。
「我的想法得著共鳴,所有力量都向我靠攏。」提起往事,王童對早期的中影經營者有著濃濃敬意:「老闆有企圖,公司願意投下大錢拍大片,追求史詩電影的規格。工作人員也有機會面對國際製片工業的潮流,學會用模型拍片的技法。當時不少三十歲左右的工作者因此開了眼界,學到一身好本領,走過七○年代的養成訓練,到了八○和九○年代才能開花結果。」他很為當今年輕人叫屈,中製、台製和中影——台灣三大片廠從九○年代後陸續消失,少了製片廠的養成與呵護,年輕人跌跌撞撞摸索前進,渾身是傷還未必能學到本事,這也說明了他何以如此看重台南岸內影視基地,因為他就是個在片廠中長大的孩子。
王童藝專美術科第一屆畢業後,沒像其他同學那樣到學校做美術老師教書,寧願進入中影,跟著曹莊生師傳,從學徒做起,一方面是美工酬勞遠比美術老師收入多。另一方面則是可以親炙大師風采,從實務中累積經驗與本事。
當時香港邵氏公司導演袁秋楓來台拍攝《山歌姻緣》,曹莊生指派他去畫一些內搭景需要的美術窗格,看他做得認真規矩,美術前輩鄒志良進一步把他從練習生升成了助理技術員,讓他有機會認識了李行、李嘉、白景瑞、張曾澤、周旭江、宋存壽等老一代名導演,領受他們像神一樣的威嚴,也在他們鉅細靡遺的嚴格要求下,學會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逐步體會如何與建築、空間產生互動,又如何在服裝和色調搭配上產生化學效應。
或許因為表現靈光,獲得賞識,王童不時有機會能與導演同桌吃飯,在閒談中聽一點是一點,累積不少獨門心法。「從二十二歲磨練到卅四歲,前後十二年的時間,根紮得很深,從劇本、美術、攝影到燈光,雖然不敢說全盤的電影功夫都會了,至少學了六成功力,都是最珍貴的現場實務。」王童從不諱言這段片廠學徒時光,為他開啟了無數創作靈光。
例如他就從李翰祥的《八十七神仙壁》拍片現場,學到郭軔老師的「假透視」技法,明白如何在小小的攝影棚裡,創造出看起來既深且遠的錯覺空間。中影大攝影棚長不過一百二十呎,寬度則約八十呎,王童在《策馬入林》搭的舊廟場景,先給了山坡陡度,近景有水塘,窗外又有林木樹景,層層鋪排後,就給人場景深遠的錯覺。

至於「做舊」本事更是每位美工的必修課,當初跟隨鄒志良老師在中影攝影棚搭起《秋決》的牢房景,所有的柱子都得一再火烤塗漆,歐威的手銬腳鐐全是厚木純鐵打造,「道具真了,演員情感就真了」的心法,日後就過渡進《策馬入林》和《無言的山丘》的美術質感。
他也曾與胡金銓合作《天下第一》,拿下金馬獎最佳服裝設計(同時入圍最佳美術設計),王童最津津樂道的卻是大導演每天到故宮看畫臨摹的認真,看到他用工筆畫下服裝道具樣式,即使只是小官吏的折帽都能從折疊或薄紗材質,清楚說明其實用特性,從中明白電影美術並非只強調形式上的美觀,因為「材料一旦真實,使用目的亦很清楚明白時,厚度和重量就不同,演員穿戴起來就有身歷其境的心理認同」。
每天混片廠,每天被大導演名導演「電」,也讓王童練就了雜抄百家的雜學身手。他形容李翰祥的電影有如美術家在說書,強調華麗與層層轉進力道;胡金銓的作品則如水墨,重意境,構圖簡略樸實。李翰祥很嚴厲,拍片絕對不准遲到;胡金銓則是沒天沒夜,好像大家都不用休息,只能拚命工作;白景瑞是輕鬆又浪漫;丁善璽最擅長調度大場面……每天周旋在不同風格的導演間,水裡來火裡去,日後再多疑難雜症也都難不倒他了。
不過,王童最「務實」的成就在於他深知「為了美術而美術是不對的,美麗的畫面,再美也不過像是彩色月曆,不能帶給人們感動的力量。電影中的美術不是用來唬弄外行人的,看似平淡素穆,卻有硬功夫,內涵其中才是本事」。以《看海的日子》為例,就有人挑剔王童搭的妓女戶,走道太寬也太明亮,欠缺那種暗黑,狹窄、陰溼又侷促的空間壓迫感,「我參觀過妓女戶,體驗過那種空間壓力,可是電影搭景為的就是要拍攝,要預留攝影機進出空間,不能只是一比一的場景復刻」,現場的體驗感受終究得回歸觀眾席上的視覺感受,場景大小或許有些許出入,然而透過美術擺設,演員肢體互動與鏡位擺設,再透過剪輯,妓女戶中小通道和小房間的暗、溼、悶、擠、困的感受,依舊能夠直接透過銀幕光影直逼觀眾心靈。

王童更相信:「好電影,總要能撩起觀眾的衝動,繼而有回味的空間,讓觀眾細品創作者意欲傳遞的訊息。」由景寫情,無疑就是王童最嚮往的創作意境。一般妓女戶沒有窗子,《看海的日子》卻特地為主角白梅挖了個窗戶,那天雲雨方歇,恩客穿衣離開,白梅起身掀開窗簾,恩客正沿著窗前小路離開,看著恩客背影,白梅一句話都沒說,但觀眾似乎都明白了,他是白梅的最後一位客人,她要告別妓女戶了,她確定自己將懷著這位客人的種開啟新人生,她的目光似乎是在和孩子的爸爸道別,也在告別自己的妓女人生,一場景包含無數心中話,這種高密度高張力的空間詩情,就是王童最自傲的成績了。

美工出身,提到片廠,提起拍片,總是格外有感,回顧自己走過的拍片人生,王童說:「我要拍的是時代,不是家族故事。我只是基於再不做,就沒有人做了;再不做,歷史就空白的信念去創作。我想拍「台灣三部曲」的動機就是替台灣寫歷史。台灣近代史從原民世界,歷經荷殖、明鄭和大清統治,再到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手,一九四九年又成為國共戰爭的前哨,戰爭陰霾始終揮之不去,我最想替政治夾縫中的庶民說話,說他們的故事。」早期的台灣電影創作備受政治干預,日治時期的台灣往事,以及一九五○年代前後的戰爭離亂及白色恐怖議題,都因為「政治不正確」,成了創作上的禁忌,不能踩,不能碰,「一九四九年的動盪人生,小說有人寫過,但是沒有人用影像留下這段歷史,用影像來書寫台灣走過的那段歲月。大時代比電影大太多了,我只是努力把電影史空白的那一個角落給補上。」其實,王童補上的不只是歷史缺頁,他在「台灣三部曲」中建構的美術時空已經成了時下對日本大正、昭和時代文物和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台灣風景的文化指標。這位在製片廠成長的電影人,衷心期待終究能有個國家級的大製片廠,「歷史建物有實體見證,還有足夠空間可以換搭當代或者未來時空的新景,最重要的是資源不要重疊浪費,就讓岸內成為書寫台灣歷史的拍攝基地,要拍海景就到台中造浪池。」
他的片廠夢,其實就是他這一輩子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