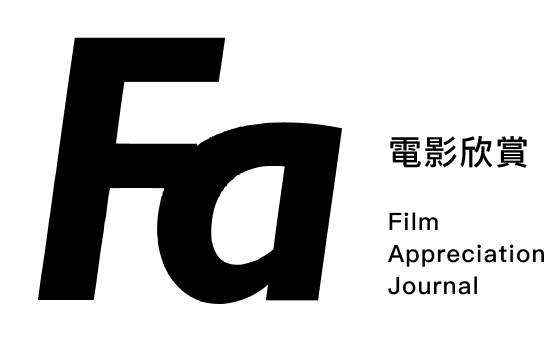專訪黃春明談芬芳寶島

專訪黃春明談芬芳寶島
黃春明
一九三五年出生於宜蘭羅東,曾任小學教師、記者、編輯、電台主持人、廣告企劃及導演等職。他的文學創作跨足散文、新詩、劇本及兒童文學等不同文類,作品關懷的對象包括鄉土小人物、城市邊緣人,九○年代則特別關注老年族群。近年除專事寫作,亦致力於歌仔戲及兒童劇的編導,曾獲總統文化獎與國家文藝獎。
「芬芳寶島」系列作品
1975《大甲媽祖回娘家》
1975《咚咚響的龍船鼓》
1975《淡水暮色》
1975《恆春一遊》
《恆春》(未播映)
日期─二○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地點─黃宅
「芬芳寶島」系列豐富的主題及影像,不僅影響了台灣後來紀錄片的發展,也為後世保存了視覺的記憶,這一切的開始,源自於黃春明所提出的拍攝計畫。本篇訪問從黃春明的廣播經驗談起,透過訪談,我們將更了解他在生活中受到了什麼樣的啟發,動念推動了這系列的計畫與後續執行拍攝的情形,以及不論是廣播、文學或電影,推動黃春明的,始終都是來自認識及思考這片所生長土地的熱情。
請您分享在宜蘭中廣電台的工作經驗。
─
我在民國五十二年(1963)退伍後進入宜蘭的中廣電台,當時在早上七點主持一小時的台語節目《雞鳴早看天》,並且和太太共同主持二十五分鐘的《街頭巷尾》。《雞鳴早看天》當時是片頭先出來,有一個opening (music),再談今天要講的重點,穿插過橋的音樂,也有的是邊講話邊加入背景音樂。後來我的聽眾很多,他們就希望我不要放音樂,從七點講到七點半,不然(聽完)上班會遲到。所以從這一點,你就知道聽眾對我們(廣播)講話的一些內容反應。我講得比較活,將生活的事件當作材料,不跟他們談理論,假如說現在有一部新電影,那麼我就會說這裡有沒有去看、我的看法是這樣,不是替電影做廣告。
《街頭巷尾》的進行方式呢? 您有去外面錄聲音對嗎?
─
我覺得(這樣的構想)是從一個理念開始,理念就像你的原則。我那時跟電台講,播音員特別是女性最受歡迎,但一直是悅耳的聲音,再好聽都會膩。如果每天能有不同人的聲音出現,那才生動。所以你就要走出去,去錄音。廣播不是只在播音室裡把外面聲音隔絕了、傳不進來,只有我們的聲音出去,那是很狹窄的世界。你的錄音室可以很大、很寬廣,需要的聲音都可以進來、播出去。
當時到各處採訪,現場錄音回來播,我騎摩托車差不多宜蘭十二鄉鎮都跑透了。舉個例子,我交代要割稻之前先趕快告訴我,電話一來我就帶著大型盤帶錄音機,到現場把割稻和打鼓機「卡卡卡噹」的聲音都錄下來,然後再把機器移稍微遠一點,襯著背景割稻聲,對錄音機說:「各位聽眾你有聽到嗎? 我們宜蘭在割稻子。」接著採訪農民,問他為什麼其他人都還沒有割稻,你提早那麼多? 原來種稻也是一種賭博,因為風雨影響都是運氣,而且稻子也有長腳種、矮種之差別。藉由這個錄音我們告訴聽眾,聽到收割的聲音,這個就是好事。雖然可能只是淡淡的喜悅,但也很愉快,還可以順便介紹稻子的種類。
再比如說有一次宜蘭水災,我也是第一個跑現場,採訪一位奶奶。奶奶家的牛都被水沖走了,她哭著問不出什麼話,當然我們也很難過。廣播出來不得了,捐款好多。隔天早上廣播我特地安插了一段,跟聽眾說我要讓大家聽到一個很溫暖的聲音,接著就拿出瓷盤,把裝了很多銅板的撲滿剖開,「啪啦啦」滿滿銅板掉落的聲音,然後向聽眾說明,昨天晚上一名才七歲的小孩子跟他家人來到電台,為了救災捐出他蒐集一年的大撲滿,我們也為此做了簡單的訪問。哇! 後來捐棉被捐什麼的,都送到我們電台來,軍方借了幾部吉普車,裝得滿滿的。很多事情就因為你把現場狀況播出去了,錄下哭泣或割稻的聲音,讓聽眾有現場感、臨場感,後來他們說,「黃先生你那個錄音《街頭巷尾》,我感覺(事情)好像就在我的眼前發生。」我就覺得很受鼓勵。

《街頭巷尾》很像您後來在拍紀錄片的樣子。
─
對,但那時候根本就沒有想到紀錄片這樣的事情。只是有這樣的理念,產生如此的社會功能,我自己都很感動,但你也會碰到一些政府不喜歡的社會新聞。後來有一次在電台會客室遇到老太太來找我,向我哭訴說她兒子明明還在當兵,卻死在羅東分局拘留所裡。一問之下才知道他過年休假回來看電影,跟人家爭吵,因為罵了比較不好聽的話,馬上就被帶走。我就到警察總局做訪問,問秘書長、拘留所值班人員等等,根據他們的報告,衝突後晚上只是把他暫時性留在分局,打算改天叫憲兵隊來,哪知道他晚上就在拘留室裡自殺,把自己的制服撕成一條布上吊。因為他當兵前是水泥師傅徒弟,我去採訪師傅,他還開心讚美自己的徒弟。從那一天開始,整個宜蘭縣警察局、刑警,還有認識我爸爸的(時任羅東的消防隊副隊長),就說要找我吃飯,要談談事情,我都拒絕。總之所有的訪談都錄音下來,晚上回來剪輯製作,但是地方台長說不能播,我當時還反問:「為什麼不能播? 我們新聞記者,就是要播報社會裡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在電台打過架,所以他們有點怕我,後來總經理就打電話來,他說:「站在朋友的立場,我讚美你這樣的工作態度,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宜蘭廣播會飄到中國大陸那邊去,你這個消息一出去,那邊會怎麼看待你這個題材,這樣對我們台灣不好。所以從此觀點,我站在國家、工作的立場禁止你。」我就不幹了,離開中廣。
您那時候寫廣播稿子是否要被審查?
─
關於審查,我們那時其實自己心裡就有個警備總部。因為(播音室)外面門上poster,就寫了:如果我怎麼樣強用電台,就槍斃;怎麼樣怎麼樣,就槍斃。三大條警告標語就寫在大門口。
您後來去電視台工作, 像是在中視就製作了節目《貝貝劇場─哈哈山樂園》?
─
我因為剛才那個事件離開中廣,但去電視台前還有在廣告公司工作過一段時間。當時因為禁說方言政策,只能在中午十二點到十二點半做(台語節目),台視那時段放黃俊雄的布袋戲,不得了,收視率百分之八十以上,連知識分子本來不大喜歡布袋戲的也會收看,為的就是聽台語,因為演布袋戲的台語很溜,又很幽默。所以台北市的路邊攤只要有一台黑白電視機,中午就滿滿的人在那裡邊吃邊看,我家小孩子也會看。比如說,布袋戲裡面兩個對打,其中打輸的,就在旁邊嘔嘔嘔,對手問是怎麼樣,他回:「沒有,我就吐檳榔。」再被對手嘲笑:「哈哈你會死了,吐檳榔!」其實就是吐血故意講成吐檳榔。後來我也常常這樣咳嗽的時候,我家小孩就會說:「爸爸你要吐檳榔喔。」我心裡就笑這個布袋戲對小孩子一點意義都沒有。我想國外puppet那麼發達,他們童話那麼多也會如此搬演,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演一些打架戲碼? 後來我知道NHK有個兒童偶戲節目《ひょっこりひょうたん島》(突然出現的葫蘆島),做了六年,大人小孩都愛看,我就跟公司建議,找了沙田倫太郎跟片岡倉來合作設計(杖頭木偶),我就寫劇本,整個故事九十二集。

為什麼叫「哈哈山」,因為我設定有一位很老的爺爺跟孫子華小海,華小海向爺爺說:「山那麼多,能不能送給我一座山?」爺爺說沒問題,就問他要做什麼,華小海說要做一個小孩子來很高興、會哈哈笑的樂園,所以叫哈哈山。山裡可以做世界上最長的滑梯,從山頂一直滑到山下這樣,還講了很多的構想,爺爺就把山送給他。孫子跟山裡的動物一起開發山,但是有一個海盜來搗亂,因為海盜只有單眼所以叫獨眼蛇,禿頭尖尖的。獨眼蛇的助理叫做小瓜呆,小瓜呆的設計後來還被餅乾公司拿去用。而為什麼海盜要來哈哈山破壞,是因為他只拿到一半的寶藏圖,另一半在這座山裡面,但小孩不知道,所以兩方就有一些衝突,不是武力上,就是搞破壞。不過獨眼蛇想要破壞東西,小瓜呆卻越幫越忙,後來小瓜呆很受喜歡就變成主角了。
各種動物我都有寫歌,例如因為很重所以被叫做八噸將軍的短鼻象、還有鴕鳥等等,現在連歌譜都留著。那講到太陽公公下山這件事情,我就被調查了。在布幕上太陽要下山的時候,會沿著山像滑梯一樣慢慢地下去,那時動物看到就說:「小海、小海,太陽要回家了,我們跟它回去好不好?」小海說好,要大家快點。於是小孩跟動物一個個爬上來,因為逆光變成像皮影一樣的黑影,邊呼喊:「太陽公公等我們一等!」太陽本來要下山了,就真的等他們,等大家堆在一起才一起下山。哇! 結果不得了,他們說太陽是毛澤東,然後海盜像蔣中正。我覺得很冤枉,海盜本來就有這樣獨眼的造型。
您之前說曾讀過保羅.羅薩的著作,啟發自己後續對紀錄片的看法,能否與我們分享?
─
以前我自己亂買書亂看,就讀到保羅.羅薩的日文版。我所知道的,一九三○年代國際經濟危機,美國失業率飆升,報導文學跟紀錄影片才開始。那羅薩是最先開始紀錄片拍攝的,那時候拍攝就一直提他的理念:紀錄片對一般人來說,就是社會的良心,應該站在同情、有人性的一面。它也應該是事實、客觀的,你要有一個觀點,再客觀地拍攝那個事實。 以我所知,因為他好像拿了企業的錢去拍,反而對企業變成一種社會良心的包裝,拍出來雖然有批判,卻對那麼辛苦的勞工剝削,結果他拍紀錄片的地位就沒有像以前那麼崇高。
您還記得在哪裡買到這本書的嗎?
─
我在三省堂書店買到,就是一本handbook。我以前還有訂日本的雜誌,例如《中央公論》跟《世界》,前者比較右派一點,後面就左派。

您知道保羅. 羅薩其實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嗎? 您有閱讀過相關社會主義書籍嗎?
─
知道。以前在台南師範的時候被老師趕出去,不能上課,所以我就去圖書館看書。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很多書架都空著,但是書架最上層有一包一包綁起來的東西,我就拿椅子把它抱下來看。包裹是用報紙包著,報紙都泛黃了,用塑膠繩綁起來,外面寫了兩個字「禁書」。如果不寫禁書我還不理它,一寫禁書我就想看了。我看了一本政治概論,一本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跟恩格斯寫的。第二頁它就寫:「窮人唯一的財富就是手銬和腳鐐。」我那時候的感情就哭出來了。那本書好喜歡,直到當老師都還在看,但是有一次下雨,我們校區那裡過去是沒有橋的堤防,當我帶學生過去、剩我自己要過時,滑了一跤,跌了一下,那本書就從懷裡溜走了。
以前自己就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對美國印象極不好。別人說globalization, 我說不是,絕對都是美國化。你看美國打贏二戰後,就像一個企業廣告,「Made in USA」,美國做的(產品)絕對是最好的。我們台灣已經對美國崇拜到說,像老人家就會反問諷刺:「美國的月亮,還比我們的月亮亮嗎? 美國的大便是可以做味噌?」所以在那時候,真的覺得美國很糟糕。
請您分享「芬芳寶島」計畫緣起。
─
就因為記得保羅.羅薩說的理念:紀錄片是社會的良心;後來又看到日本的《DiscoverJapan》,特別令我印象深刻。我常常講我到政大經過興隆路,右手邊都是稻田,結果要去住宿的大學生,看到車窗外的稻田竟然問說:「那是什麼草?」這問題很嚴重,他連稻米都不知道。台灣年輕人對台灣自己都不知道,讀大學有什麼用? 太重視升學主義、考試主義,結果年輕人跟社會都脫鉤了。所以我想應該以各方面介紹台灣,人家Discover Japan,我們是Discover Taiwan,介紹台灣是什麼樣子,幫他們發現台灣,重新看這個鄉土,所以才寫「芬芳寶島」一系列計劃。
您本來是寫五十二集對嗎?
─
後來沒有辦法拍那麼多,一個禮拜要一集,我這個神經病。我那時估價六萬五(一部片),結果節目經理顧英德就說我這個瘋子,這樣不會成,九萬五好了。我還跟他說九萬我也拿,結果最後累死了。不像以前拍片NG也沒關係,我若NG丟掉(片子),都是錢。而且我比較認真,多拍一點,或者片子還沒有沖出來,沒有自信就再拍一次,所以花費都比別人多。
「芬芳寶島」一開始的題目叫做「吾土吾民」?
─
那是林語堂的書名,他們這樣講的但我不知道。後來的「芬芳寶島」,也是中視取的。
您也有做「芬芳寶島」的片頭曲, 但後來沒被採用。
─
我以前有寫:「生在鄉土長在鄉土,鄉土怎麼叫人不愛,花開在鄉土果結在鄉土,鄉土怎麼會不芬芳,我們的理想我們的願望(希望),都建築在我們的鄉土上,生在鄉土長在鄉土,鄉土怎麼叫人不愛」(編按:本版歌詞以此次訪問為參考),包括旋律都做出來(現場唱起來)。 後來他們覺得,也有外省人不是(生)長在這裡,就有很多(不採用)的理由,我說好,就這樣。我認為有一些identity是天生的,有些是教育的。像日本統治那麼久,我爸爸那一代就被他們洗腦了。我對日本很多批判,有次我帶日本記者去鄉下採訪,老年人很活潑,跟對方談得很高興。記者就對我說,他們沒有像你那樣反日,我還回他:「他們是在你們那個時代長出來的,被洗腦,你可見他中毒多深。」比如二戰結束時大家在廣播機前,「玉音放送」,當日本天皇說無條件投降,我爸爸就哭起來。我爺爺罵他:「你是肖仔,我們贏了你是在哭什麼?」我爸把眼淚擦一擦,還是很嚴肅,笑不出來。就是被洗腦。所以說這個identity,我想出生地的identity 大概沒有問題,但是後來的族群認同,或者說社會國家的認同是洗腦的。
請您分享《大甲媽祖回娘家》前置調查的狀況。
─
我前一年就跟大甲媽祖走了八天。先拍照片,看哪一個地方不錯,可以拍到什麼就先拍,還記錄下沿途有哪些事情及老百姓的對話。比如說當地小攤販如果欠人家錢,來討債就習慣性會說:「等婆仔回來之後,我才還你。」婆仔回來就是媽祖回來,因為到時(來的)人很多,他就有收入。
還有整條街的信徒全部跪下來、搖著隨香旗的畫面,那真感人。這不是臨時去找的,而是前一年我就發現了,北港媽祖廟左邊的高樓,還有一個中樓消防隊很適合,所以我就先上去拍照,跟他說(允許)我們以後在這裡拍。這些都要事先了解,讓畫面自己講話,不要說明什麼。
您做了很詳細的筆記。
─
詳不詳細不敢說,但就要這樣做。其實若information documentary要變成帶有一點戲劇性的話,你就要看他們怎麼生活,或者怎麼對話。若沒有真正深入去了解你要拍的對象,就沒有辦法很生動很深刻,缺少這兩點,紀錄片的說服力也就差了。
現今留存的《大甲媽祖回娘家》膠卷是台語配音,但當年在電視上播放是國語版本?
─
是,一定要國語。台語版本是後來誰去做的我也不知道,當時國語是李季準配音,比如說最後畫面是信眾感動地回來了,就這樣一個個進來後關門。鏡頭就對著媽祖白白的臉,推一個close-up,旁白就對媽祖說:「媽祖祢都看到了?」意思是看到那群人從前幾天就一直跟隨祢、看到對祢的一個景仰。我是要這樣呈現,文字說明是一大堆,但你語言表情對的話,那個(意思)都會跑出來。李季準就是那句錄音一直讓我不滿意,他後來就說:「我是全台轉播,我的國語你在講什麼?」我說不是國語的問題,(是)語氣,後來勉強了。《淡水暮色》其實那個片子也不錯。


《淡水暮色》這部片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
我寫了兩百多張稿紙,到後來實際劇本只有用十三張。片子裡我用了「日頭將要沉落西,水面染五彩」,那麼美、歌詞也很棒的一首歌《淡水暮色》。我沒有用罐頭音樂,一定要叫人來拉胡琴,最後找了楊麗花歌仔戲班的阿添仔。一開始錄我就覺得不對勁,淡水的暮色這麼漂亮,不是你旋律、節奏對就可以的,沒有感情。錄到最後我都不滿意,阿添仔就反問到底怎樣才對,我說沒有那個感情。後來知道阿添仔晚餐都加減喝點酒,所以那天晚上就讓他好好喝再來錄音,胡琴就有一點顫音,非常好,我就覺得對了。所以紀錄片的背景音樂,或者片頭、橋段的音樂,都很重要。張照堂在《大甲媽祖回娘家》要用Bob Dylan的音樂,我就覺得不對,你用那個接地氣的(廟會音樂),咚咚隆咚鏘鏘鏘鏘,就嗨。

您跟張照堂老師當時的合作模式是如何呢?
─
我在之前寫了劇本,就跟他講我要拍什麼,把地圖(規劃的地點)給他看。
當時製作有被審查嗎? 或是告訴您什麼不行拍。
─
這個沒有,劇本也沒有。
「芬芳寶島」後來在電視上播出, 您還記得當時觀眾、或其他人給的回饋嗎?
─
因為電視公司跟我很熟,他們有告訴我說收視率蠻高的。但其實影片我沒有好好看,我怕看到生氣,因為(拍出來的成品)跟我最初的想法已經不一樣了。
您能否舉例子說明您原先企劃與後來執行不同之處?
─
白鷺鷥那部(編按:《我們的好朋友—鷺鷥鳥》),我是以宜蘭竹圍農家那裡的白鷺鷥為設定,滿滿的白鷺鷥,曾經有一次夕陽時我經過那裡,「哎齁——」這樣一喊,所有白鷺鷥都飛起來,夕陽一照,真像好漂亮的火焰。但因為DDT農藥的使用,白鷺鷥漸漸消失了,所以我就想拍白鷺鷥,講這個農藥的問題。當然農民也跟我說白鷺鷥也有被蛇吃。但國和拿去亂拍,後來他們去西門町賣書的租了一條眼鏡蛇,把白鷺鷥的幼兒塞進去,蛇沒有辦法吞就吐出來,他們就將(膠卷)倒帶變成牠吃進去。就是那個cut,我氣得要命,我說怎麼可以這樣欺騙,紀錄片絕對要事實,你那個不是一顆老鼠屎,是整鍋都是。
我要介紹動物園,也寫了一篇〈我們的動物園〉劇本想好好介紹。但他們(國和)就找簡單的,以為這樣拍就是紀錄片,所以拍到猴子就講孫悟空,拍到蛇就講白蛇傳,拍到野豬就豬八戒,就是這樣胡搞瞎搞。
還有我跟大甲媽祖走的時候,也有去拍攝北港牛墟的照片,例如把瘦瘦的牛灌水,還有用花生油把毛擦得油亮。牛市開市的時候,就在那邊拍肚子,或是用爬小坡拉車來試(哪隻牛體質好),我還記得一個畫面是牛爬得很辛苦,趕牛的就用藤條鞭去戳牛睪丸,牛一痛就爬上去了。這些我都照下來了,結果都沒有(拍成)。我也有兩個計畫要拍原住民,蘭嶼跟日月潭鄒族,而那些都沒有弄成。(編按:國和最終有執行拍攝《神奇的蘭嶼》與《日月潭傳奇》二部)
《恆春》這部留有膠卷,但好像未公開上映?
─
沒有。反正我東西就是交給他們(國和),自己不會留。
《恆春》是在講屏東的恆春半島都是瓊麻,好漂亮很特別,瓊麻跟其它植物不一樣。它葉子是有刺的,高高的,所以伯勞鳥都會來。採瓊麻的工人很辛苦,要扛著麻袋走到南灣,讓它在工廠裡腐爛,然後再用鐵夾,伸進去一夾一拉,把葉枝、葉肉刮掉換過頭來,剩下就再讓它發酵變成纖維。瓊麻的纖維可以做航海用的繩子,它不怕海水,或者若木頭船間有隙縫,也是用瓊麻塞,防止水透進來。但是當石油化學的石化原料一開發出來,瓊麻就不能用了,那裡的瓊麻一下子就被砍掉,所以很可惜。這部片我還有用陳達的音樂當配樂。
「芬芳寶島」系列推出時主打它是鄉土影集,後來鄉土文學論戰時也有很多人在討論「鄉土」是什麼。對您來說,芬芳寶島的「鄉土」是什麼意思?
─
沒有,其實很多人把我歸類到鄉土文學作家,我曾經辯駁過,我無所謂鄉土不鄉土。我沒有(刻意)把稿紙攤開想說我就要來寫一篇鄉土文學的小說,那種意識一點都沒有,要寫什麼就寫什麼。我後來到台北市,對知識分子都比較批評,崇洋媚外,例如〈我愛瑪麗〉那些。結果他們說我還是喜歡聽那一聲鑼、我寫〈鑼〉那類的。其實不是,我想文學也有文學的藝術性,當然它也要有批判性。
過了四十六年, 您覺得台灣如今還會需要一個新的「芬芳寶島」嗎?
─
我在癌症之前還買了一百五十CC的摩托車,因為我要重新再認識台灣,雖然現在不能騎了。我想真的有必要,我們對外國總是比較清楚,對自己台灣不清楚。其實旅遊不是遊戲而已,是一種很重要的學習,但我們總把旅遊當消費,就坐飛機、遊覽巴士,去住飯店,計算一個禮拜花多少錢可以去幾個國家,連走馬看花都不算。就好比我喜歡看長篇小說,第一次看的時候你記人名,好像有人跟你導覽,但你再看第二遍時完全不一樣,就像自己去玩。所以我現在回頭重看很多過去的東西,好高興,一定要兩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