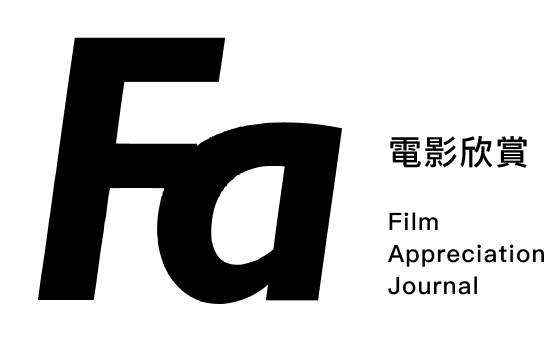如果一粒菜籽不死:重看萬仁的第一部長片《油麻菜籽》

如果一粒菜籽不死:重看萬仁的第一部長片《油麻菜籽》
提到萬仁導演,說他的作品「未被充分認識」,似乎還蠻常見─在看《兒子的大玩偶》(1983)時,我最喜歡《蘋果的滋味》。長大後,才知當年有個「削蘋果事件」,促成了「楊士琪卓越貢獻獎」。而可能被以為順風順水的台灣新電影,背後原有驚濤駭浪─這些小說與電影多是我小學的記憶。兒童時期感覺親切的電影,在長成後,是否經得起檢驗?這是我重看《油麻菜籽》(1984)的動機之一。
剪刀、婚紗、洋娃娃
廖輝英的原作節奏頗快且言語生動,她與侯孝賢都掛名改編劇本。電影是「大致忠於原作的文學改編」——不過,也有較顯著的改動。原著裡,受傷是因為父親將菜刀擲向母親,電影裡變成夫妻在打鬥中,母親的剪刀刺向自己手心。母親以剪壞女主角阿惠的頭髮,作為對她戀愛的懲罰,原著未見。剪刀出現多次,它是女性化的工具或陽具的對稱物,盛怒的女人「剪掉男人的命根子」,並非只是隱喻,也見於現實。電影中的剪刀最多及於剪壞丈夫西裝。洋娃娃在小說裡,是父親一時興致的禮物,阿惠「望住那陌生的大男人,疑懼參半」,小說刻畫父女關係的空白。電影裡,送洋娃娃接在母親流產,幸有阿惠奔跑救命之後,變成父親對自己「不顧家」的贖罪禮,在女兒穿婚紗時,又變成父女聯結的信物。
父女都要背叛母親,遂行自我的意志。洋娃娃收在櫃子裡,但眾人皆知。母親拿娃娃後腿軟,象徵了「母權跛腳」。「父母和解」是進入婚姻前的感情需求,這符合常識。不過,電影其實虛晃一招,「母跛」再次打破了三人關係平衡的假設,父親接了娃娃,從此卻在鏡外。趕去慰母的阿惠,由母親掀起了新娘頭紗——母親此時近於「前新郎」。母親並未發火——但對婚姻的恐懼揮之不去。雖然母親收發男尊女卑的論述,但真正的屈從很難存在,怨恨通常是需索公正的幽靈。
電影也放大了父母代表自由(享樂)與傳統(受苦)的對立。原著中,母親見過世面。對女兒的教育,態度是矛盾而非單一的。電影傾向將母親塑造得更加保守─如此的好處,是它可能適用更多數的女性境遇。電影中,曾為醫生之女的母親說出,想讓女兒小學畢業就去做女工,除非是對丈夫的激將,不然就算窮得厲害,也還有點違和感。拿掉小說中母親為女兒買鞋一段,刪去了最能顯示母親愛女的段落,有點可惜,但合乎這部電影「捨殊相就常態」的一貫性。
不過,這樣的比較,對電影遠遠不夠。
電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兩個部份。一是它的「如畫性」,二是它置入的「注目軸線」。兩者成功地轉化文字對性別歧視的陳述為影像。必須也為演員表現記上一筆,無論柯一正飾演的父親、顏正國飾演的哥哥,或從小而大的阿惠(李淑楨、蘇明明等人飾),所有演員都相當出色。陳秋燕所飾母親,更是驚人─老年的她,不單有受盡磨難的「被磨感」,因為女兒獨立而終於可以「由緊而鬆」的愚癡感,形成混合滄桑與幼稚的複雜氣質。

如畫電影的構圖語言
倒下的父、痛哭的草,與不同爽度的身體性
阿惠外公之死令阿惠母親心神俱裂,電影中,悲痛卻不靠嚎啕——這一幕從白色蘆草夾道翻飛的無人空景開始,但「痛哭流涕的主角」是狂風中的厚重蘆草。在這之前,電影透過拍攝阿惠外公理髮的畫面,呈現了「婚姻難救」對外公的打擊,理髮使拍攝外公斜躺與白毛巾蓋面得以嵌入敘事,影像語言說得卻是「快倒下去了」。一樁他作主的婚姻幾乎可以殺了他,用他的煩惱間接表現婚姻中的絕望,相當高明——閉眼外公眉髮濃黑兩鬢微白,從這一鏡到全白蘆葦,可稱為「電影中的伍子胥過昭關」。
男人身體常玩樂,女人身體服勞役,影像說得更多的是,前者在後者眼中的「爽度」:阿惠長時擦地板,哥哥一進來就踩髒,這一幕極好,在於速度的對照。顏正國飛竄——這是一個爽度爆表的男童身體,奔向他的玩伴爸爸。阿惠也有機會跑,但那是為了幾乎喪命的母親。

男人負責爽,女人負責救——性別分化的極致來到《油麻菜籽》最特殊的一段:不是淫婦,而是「姦夫」被迫洗門風。丈夫向外求爽的盡頭是,被逮到與有夫之婦有染,面臨道德制裁與暴力威脅。毫無招架之力的他,要妻子解救。洗門風當然是種陋習,場面恐怕相當屈辱恐怖。此節有相當多層次值得深入。電影將小說裡的「罰金」提高了五倍——更嚴重的是,舉家得流放到台北貧區。
這個「插曲」改變了家庭的部分權力結構:父親終於在家吃團圓飯了,火車站裡最像「全家福」的一鏡,「前浪蕩子」父親還抱著嬰兒(!!!)——前一場的對話暗示,是否收留父親這個「道德賤民」,母親有權決定。來到台北是「上」或「下」,並不單純。阿惠考上第一志願初中,變成父親的社會資本(同事都跟我道喜)而開始被父親「領養」─教育擴大她與傳統女性的距離,也給予她「被視為與男人平等的入場券」——這是不少女性的經驗,自有其歷史重要性。

指定注目鏡頭
是敘事,也是性別針對,更是電影倫理
柏格曼的《莫妮卡》(Summer with Monika,1953),男女在孤島上痛快擺脫社會習俗自由生活,但莫妮卡懷孕後,再受不了不囤積的「全自然」。這裡我們暫不討論懷孕造成女人「必須預備」的壓力。心理學中有種說法,「賺錢的外表之下,真正隱藏著嬰兒早期幻想中﹃取之不盡的胸脯﹄。」事實上,不可能存在這種奶水——《油麻菜籽》中充斥著「男人會花,女人猛攢」的現象,這或許與女人明知奶水會竭,卻還想成為滿足男人幻想的「錢母」有關。生過三胎的母親又懷孕了,更煩惱錢。阿惠於是取出自己的竹存錢筒。媽媽先不要,後來對她說:「錢是妳的,妳來砍。」


這段本悲催,但電影加上另一段:阿惠離開在地上撿錢的母親,轉身發現父親還在不遠處,兩人交換對望。這系列的鏡頭定性「劈竹筒」不只是「母女之間」,也「指定父親注目」——「指定注目」不只是訊息式的「他看到經過」,也是電影倫理的——父親「散仙」迫使女兒「代父從『夫』」,家人常是彼此的起源。
兩人對視如同「神秘的質詢」:你這個「父親」究竟是誰?我們算什麼?
小說文本「不甚究責」的成長敘事,電影在讓男性更少厭女的形象中重組,但這「與男性更有關係」的設計,並非美化。相反地,「指定注目鏡頭」扮演了關鍵角色,如同對男性發言:油麻菜籽,也是你的故事。見者有份,旁觀就是啟動有關。
真是想不到的台灣電影啊。
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存在兩個版本的《油麻菜籽》─台語版與普通話配音版。這個雙版本的現象,足以回顧過去的電影語言歧視。台語版的影片修復已啟動─這會在美學與性別記憶外,為我們再添一個,重看經典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