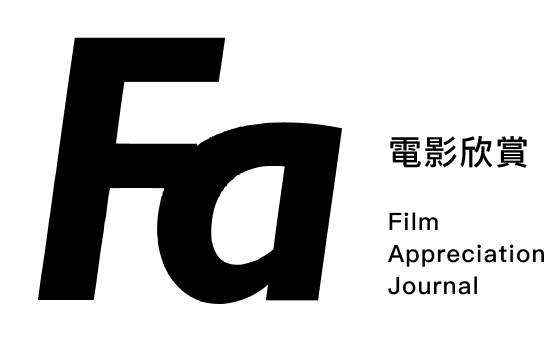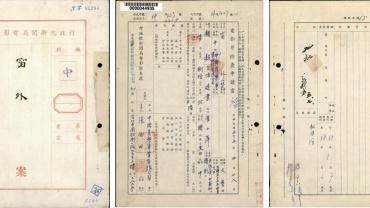電影理論與亞洲:論山本直樹的《辯證無合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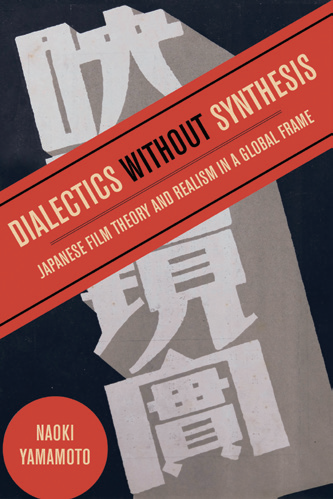
電影理論與亞洲:論山本直樹的《辯證無合成》
一九八○年代以降,思考「亞洲的(電影)理論」是東亞研究當中重要的課題,康乃爾大學的酒井直樹、交大社文所的陳光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書美都對這一議題多有著墨。大體上,這些學者都在思考「理論是否是西方思想、學界獨有的產物?」,以及「廣義的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面對理論的翻譯、移植與本土化?」如同「哲學」一詞是西方思想的產物一樣,當理論被轉嫁到東方時,依循西方學術體系建立的學院體制中的大學教授,又該如何面對本土論述在學術地位上的次等病識?山本直樹(Naoki Yamamoto)的《辯證無合成:日本電影理論與全球框架下的寫實主義》(Dialectic Without Synthesis:Japanese Film Theory and Realism in a Global Frame, 2020)即是在這類關懷下成書的作品,闡述並強調回顧日本電影理論的重要性——不僅僅要透過另一個視角來思考電影理論上的重要議題(寫實主義),同時還要面對身分政治的問題:日本脈絡是否有本質上的特異之處以及重要性?
自二○○八年的電影理論史大會(Permanent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Film Theories)之後,北美以及歐陸的電影學者開始正視學科理論北美及歐陸中心的狀況。多數電影理論課程選用的文章可以大致以斷代史分為兩類:一九七○年代以前或是以後。七○年代以前的文章,多以美國知識份子(孟特斯堡﹝Hugo Munsterberg﹞、林賽﹝Vachel Lindsay﹞)、法蘭克福學派(班雅明、克拉考爾)、俄國蒙太奇理論(艾森斯坦、維托夫)、法國《電影筆記》選輯為主,七○年代以後則是完全將目光放在英美學界所產出的文章與書目(加上兩本德勒茲)。從這般安排看來,我們甚至可以說隨著電影研究進入學界,人們所閱讀的理論變得越來越狹隘,或是僅僅把外於歐美的理論研究當成在地化的成果。也因此,近幾年來許多回返早期電影理論的嘗試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比如說,在歐洲語境下,許多二十世紀早期德國影壇的思考集結在《電影的承諾》(The Promise of Cinema, 2016),義大利影壇的則出現在《早期義大利電影理論》(Early Film Theories in Italy 1896-1922, 2017),都讓人們對於歐洲各國對電影的思維有更細緻的了解。
除了理論歐陸中心的問題以及第三世界論述的邊陲化以外,亞洲語境還有電影史的問題需要處理,意即多數國家的電影史仍是支離破碎的狀態——中日兩國早期電影多數都已然佚失——更別提許多殖民地都是在二戰之後才能說真正有了擺脫帝國箝制的電影發展,因此相對應的論述起步也就更晚。現代化的落差讓歐美(日)的論述成為亞洲電影理論的啟蒙與必須回應的對象,而亞洲的電影——像是薩亞吉雷、小津到晚近的侯孝賢——成為藝術現代性的旗手,為西方的理論施肥。因此,亞洲電影理論史以及其後來者的身分在學界就更加無法受到重視,隨著電影研究進入北美學界以及亞洲學界,某種理論的正典心態當然就成為一片蛛網向外擴散,成為全球知識生產結構的枝葉。山本的優勢在於選擇了日本做為研究對象,透過亞洲電影和電影論述史最為完整的國家來回應這些「晚來者」的問題,並透過日本與其他國家的知識交流重建日本電影理論的特殊之處。
現代性的移植讓寫實主義成為日本電影論述當中的重要主題,山本透過五個章節詳述了從二十世紀早期到二戰後寫實產生的不同意涵,這代表了他並不將「電影寫實主義一詞指稱電影史上已經被當作『寫實』的特定電影技法或是敘事模式」,他用此一詞彙是為了「涵納更為廣大(也無疑地是跨國)的論述框架,目的是透過電影媒介以及其特定的媒介形式來表達二十世紀現代性的生活經驗」(p.15)。比如說,在二十世紀早期,日本語境下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脫離不了關係,然而自然主義並不僅是左拉筆下宿命式的科學描述,而是轉為捕捉「如其是」(ありのまま)的心態。社會學家権田保之助就認為電影如果能夠更多地使用自然以及日常生活當中的元素,也就更能夠調動我們的直覺,與世界無法表達的真理更近一步(p.35)。到了一九二○年代,此般心態也隨著關東大地震還有日本電影的現代化有了不同的意涵——拋棄男扮女裝的歌舞伎傳統,拍攝新劇都是為了更貼近日本人當代的樣貌,挑戰好萊塢對於異文化的醜化,並以文化輸出為主要目的的「寫實訴求」。
第二章談蘇聯的蒙太奇理論如何進入日本知識界,分裂、轉化成為「機械美學」與「無產寫實主義」的爭論。第三、四章則是聲片的來臨如何引起一波文學改編的熱潮,以及對於日本進入軍國主義時代再現歷史敘事的焦慮,尤其是紀錄片這個類型在一九三○年代的日本影壇當中如何受到政府的鼓動、引導與管控,成了呈現帝國光榮的「文化電影」(文化映画)。第五章則深入探討了帝國檢禁下,生活/歷史的寫實無法成為探討的議題後,評論家如杉山平一、長江道太郎如何受到京都學派等哲學思潮影響,往內在探索寫實的可能性,以現象學的懸置避開面對時代的囚籠。這些章節有效地為我們繪出日本知識界對於電影、現代性和寫實主義的思想轉變,同時間把抽象的大寫理論拉回特定的時空、風土脈絡下賦予其血肉,把「如、其、是」三者的意涵脈絡呈現出來。
如此的書寫進路雖然有實際上的用途——讓我們有不同的文本可以放進課程中——同時也引出兩個關鍵的問題。一是「沒有電影的電影理論史」,也就是說書中種種寫實主義的爭論,似乎沒有辦法為我們分析電影帶來什麼明確、實際的洞見,好似西方理論雖然不是唯一的理論,但卻仍佔領著美學的金字塔。換句話說,當電影理論少了電影研究的文本,其理論話語到底能給當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另一方面,回頭思考全球電影思想史的演變時,我們似乎將「理論的正確性」放在一旁,只透過某種媒體考古學的方式聚焦在「理論的可能性」以及現代性時間的前後差異(「早了巴贊多久……」),那麼理論要如何回到當代來面對我們現下的爭論?
當然,重返特定時空背景的理論爭議在台灣電影的研究當中也不少見,尤其是許多學者都處理過寫實主義在台灣/電影理論在台灣發展的脈絡。然而,或許我們可以為進入台灣的電影理論,增加歷史的向度,討論全球化下學界的發展:我們是在什麼時候,用著什麼樣的理論,討論什麼樣子的電影?從一九八○年代末以來,留法、留美的學者逐漸回到台灣學界,並把精神分析、文化研究、形式分析逐漸帶回台灣,他們用了這些理論是為了面對什麼樣台灣電影論述上的問題?為什麼寫實主義和侯孝賢似乎有論述上的親緣性?楊德昌又怎樣透過詹明遜和後現代的美學浪潮有了糾葛?這些後設的理論史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想像「怎樣的理論能夠回應現下電影急迫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