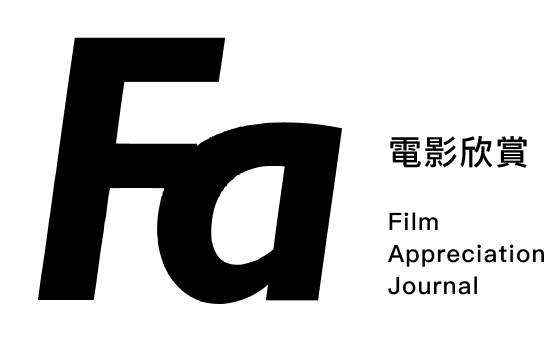歲月.紀錄——訪張照堂

歲月.紀錄——訪張照堂
*本文出自張照堂音像作品研究暨出版計畫(2015),資料提供:台北市立美術館。(註1)
林木材(下稱林):想請老師談一下關於電影、音樂等啟蒙過程?
張照堂(下稱張):有看過一些東西,如安迪.沃荷(Andy Warhol)實驗片的文字論述,像他拍摩天樓,一部很長的片子,但幾十年後才看到影片本身。在電影院看的電影,有義大利寫實電影的維斯康堤(Visconti)、狄西嘉《單車失竊記》,當時看了很感動,因為畫面是黑白的庶民生活,看到就覺得是相當好的一部電影,還有英國的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的電影,受那些影響蠻深的。
我印象中最早聽音樂,是升高中那年(1957)到南部親戚家一個月。當時家裡收聽美軍電台播Bob Dylan、Simon & Garfunkel,印象很深刻,好像第一次聽到非常能代表年輕人的聲音,他們不是流行的靡靡之音,當時有人稱「新搖滾」、「新民謠」,除了歌詞外,整個演奏技巧或精神上是屬於比較新、現代的感覺。所以我對那些音樂蠻著迷的,開始越聽越多,後來慢慢延伸聽其他音樂。
音樂跟影像一樣是國際語言嘛!一旦有歌詞加入就比較侷限,像是對歌詞的理解或語言特性,如果不屬於同族群的話,會比較難進入,所以後來我用很多地方的音樂,但也會用那些有歌詞的音樂,早在七○年代前中視剛成立時,我負責「新聞集錦」,會把我那時喜歡的新民謠或新搖滾放進節目裡。可能是填充用只有三、五分鐘,找一些我喜歡的歌曲,然後再去拍跟這些歌有類似情感或調性的畫面,把它配在一起,加起來也覺得蠻好玩。很多觀眾第一次有機會聽到這樣的音樂,也很新鮮說:「東方跟西方的音樂怎麼會這樣結合起來?」結合起來還蠻和諧的,所以他們也覺得蠻好。
後來影像上用的音樂,其實就不是那種所謂新民謠,它是另一種,我稱它「進步音樂」。這裡其實綜合了所謂民族音樂,包括所謂爵士、新爵士這些東西都混在一起,非常新鮮、有創意,跟你要用的東西又能結合,所以後來是用這種音樂。
林:我們現在熟知的《王船祭典》音樂版本,在當時播出民眾反應是:「我們燒王船的時候,不是這個音樂。」、「燒王船哪有慢動作?」,後來又做了一支帶旁白的版本。這兩個版本,一個是比較主觀的詮釋,去講精神上的東西,可是相對的另一個版本更像在地觀點、更有資訊。你做紀錄片節目時,有沒有曾被這兩難所困擾?
張:有不同的考慮吧!有時覺得你要報導的事或人,應該要站在旁邊,安靜觀察報導就夠了,不能加主觀情緒;有時不是屬於這種面向,我覺得就可以加入自己的某種情緒,讓要報導的東西稍微有點個人創意,或另一種觀看方向,我覺得要根據你做的節目跟題材啦!
《王船祭典》是因為看慣太多民俗報導是從頭到尾把發生的事報導出來而已,講了一大堆旁白,一點都沒有新鮮感跟創意,所以那時我才會拍完以後,就把它擺在那邊一、兩個月都不動……因為還不曉得該怎麼做。後來想說之前在新聞局做過類似MTV,用音樂來詮釋影片的方法,所以我想:「好,我還是用音樂來詮釋。」就去找音樂,正好那時Mike Oldfield(註2)的音樂非常有意思,運用各種民俗樂器、以搖滾跟前衛的作法綜合很多東西,更妙的是音樂在唱盤上是一整面一條歌,當時很少見,再加上音樂有起承轉合的變化,所以很特別。我把唱片拷成錄音帶,然後再拷到錄影帶上,從影像上一段一段去找切入點,加強中間的變化。根據音樂變化,我反覆去做也許是回溯、也許是前面的整理剪接,但整個過程還是有《王船祭典》從頭到尾的次序在走,只是中間偶爾跳一下回溯的東西。
播出後,當地居民就打電話來說:「怎麼搞的?看不懂。」我說:「沒關係啦!因為我們只是做一個我們想做的,過兩個禮拜會再播一個你們想要看的。」那個版本就是現場聲音加一點旁白,比較像一般的民俗紀錄片。 所以你說《王船祭典》是紀錄片……它就是個影片嘛!你也可以說有創作性,可是它的創作性又根植它所記錄的真實,只是運用技巧讓它達成另一種效果。
林:從「六十分鐘」到「映象之旅」,我發現大部分的攝影風格是手持,包括拍攝藝術表演時也是手持。像現在的電視其實講求鏡頭穩定,所以都會用腳架,可是當時你卻選擇大量手持,某種程度也變成一種獨特風格,有沒有特殊的原因?
張:因為若要固定拍,第一是機器很重,然後會需要很多人,腳架拍攝要移動真的是不方便,很多事情發生時根本來不及跟,所以必須手持,以最快的反應去拍那些東西,所以那時的著眼點就是盡量讓影像活潑,不要太死板。如果真的要拍一個精彩活動,乾脆派電視去轉播就好了嘛!
我們用小攝影機,基本上當然是手持的。我也比較喜歡手持那種機動性及迫近性,如果固定在那邊,你永遠保持一個距離冷冷地看,可是你用手持迫近(被攝者),你靠近地拍一個人在講話,比較可以看到他的性格,若你離得很遠再zoom in去拍,那個個性就被冷掉了。我拍的時候喜歡盡量看到人的性格或某種特性,所以靠近他是好的方式。
林:《紀念.陳達》其實跟「六十分鐘」《往日情懷李光輝》的片段是一樣。事實上老師安排了陳達跟李光輝碰面,然後陳達唱了一首符合他心境的歌。我發現這個畫面裡其實還藏有一件攝影作品,雖然我們現在稱為紀錄片,可是在當時這個鏡頭裡,它就隱含了一種安排的元素。

張:這是我拍我姑婆的照片,然後把它放在「稻草人」咖啡廳裡。陳達在那邊唱歌,我常常去「稻草人」就順便幫他拍點照片嘛!因為(畫面)從那邊轉換到這裡來,我不能直接跳過來,所以用那張照片轉換。
那時去找李光輝是因為有興趣想拍他,知道他來台北參加「老人遊台北」活動就特意去找他,我記得當時拍的東西還不夠多,想說找他去晃一晃,可以再多拍點東西,馬上想到陳達,因為當時我也在拍陳達,我就帶他到「稻草人」跟陳達說這是誰、他有什麼故事,他差不多想了五分鐘之後,就唱出他的身世,然後幾個七言絕句還帶著押韻。陳達厲害的地方就是你告訴他一個故事,然後想一下,他可以馬上把你的故事用押韻敘述出來。所以就變成兩個完全不同族群、遭遇的人,用歌聲把某一種感情給拉近吧!這個當然是安排的,你不這樣安排,根本沒辦法同時拍到兩個人,包括陳達在關渡唱歌也是安排的,我想帶他去逛一逛,然後順便拍點東西,就把他帶到關渡,坐在船上,請他唱歌這樣子。
所以很難得啦!因為你沒有安排,可能就看不到這樣的畫面,雖然有點怪,但我覺得蠻有意思的,一方面可以展現陳達唱歌的能力,一方面讓李光輝也經驗到另一種場合,你看看李光輝那個表情……他也完全聽不懂,好像一直猜測在唱什麼,因為他連國語都聽不懂了,可是我覺得他可以從他歌聲的苦澀裡,感覺到其實唱的就是一種生命的經歷,我相信他也知道兩個人有著相同的歲月滄桑感。
林:在拍紀錄片這件事上,其實沒有什麼規範?
張:沒有規則啦!任何事情都沒有規則,紀錄片、劇情片哪有規則?只要你把你要的東西表達得更好或更豐富,然後看起來並不違和,其實OK的,你不要很刻意,那就有點怪,你要想辦法讓它盡量自然就好。
林:1988年,你跟胡台麗、李道明老師一起合作《矮人祭之歌》,但在之前已經先看過《神祖之靈歸來》(1984)(註3),然後在報上評論談紀錄片迫切需要什麼,批評當時電視製作型態太趕或根本沒有貼近現實。《神祖之靈歸來》對你來說可能也有一些特別意義?
張:第一次看到一個中研院學者,雖然不是紀錄片工作者,但她願意自己去拍。不過《神祖之靈歸來》是跟台視借很笨重的機器,並不容易拍攝,她也不太會使用,所以攝影很不好,可是她對原住民的態度、拍攝內容的表達上很專業。你會覺得感動,因為在那個年代還沒有一位學者或專業人士,能花那麼長時間去拍出來,那種精神與態度是可佩的,所以我也很支持那部片。她有找我看片聊一聊,後來就找我去拍《矮人祭之歌》。老實講,我用的還是中視的攝影機,利用一個休息時間去幫她拍。拍的時間不長,矮人祭之前去拍一點,然後正式祭典時拍了兩天,整個拍攝時間也不過一個禮拜。李道明負責錄音,胡台麗負責編導,最後這個片子就這樣形成了。
林:胡台麗具人類學、民族誌背景,這也是老師第一次擔任紀錄片攝影師,可不可以談一下跟電視紀錄片拍攝經驗上的不同?

張:喔,當然不一樣。你知道她已經花那麼長時間在研究這個題目,所以是可以信賴的。若我們自己去做原住民題目,絕對沒有那麼長時間田調,去瞭解所謂的原住民祭典,所以這方面當然都聽她的,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矮人祭當晚,當地居民喝酒、跳舞,拍到一些原住民酒醉吵架的情況,後來遭到批評,說那些片段凸顯原住民愛喝酒的壞習慣,胡台麗當然去解釋了,她說其實這是現實,有這樣現象,不應該為了什麼去避免。當然這是可以討論的,但對原住民來講,就覺得這樣會留下不好的印象,誤以為原住民喝酒一定會吵架。那些爭議當然也都是好的,因為基本上他們站在紀錄片倫理去談這個東西,可是胡台麗也有她研究人類學的立場,不能因為這些是缺點就避掉,所以這東西當然見仁見智。
林:老師曾說過「攝影是遺憾的藝術」,相對於攝影,老師會怎麼形容紀錄片?
張:老實說,紀錄片從某個觀點來講也是個遺憾的藝術。其實所有的藝術在表現方面都是遺憾的藝術,尤其是攝影跟紀錄片,當你有心想把它做好,但可能正好在那一塊你沒辦法做好,或那個環境有缺憾,沒辦法做到。以文學、繪畫、音樂這些創作來說,比較不會受限制,你受限制的可能是個人的某一種能力而已。可是攝影跟紀錄片,因為有要拍攝的對象,要對他負責,要考慮對他有沒有造成什麼傷害,可能在某種情況下便沒辦法把握時機,因為這跟時間有關,這些都會變成某一種遺憾嘛,對不對?不像個人創作完全投入、完全自由,你還是有個被控制的、要接受與面對的一個目標,被拍攝的人也好,事物也好,有某種關係,這個會造成某種遺憾。
做得好的片子,能真正呈現某一種生命裡、真正的本質跟底層的東西,那就非常動人,因為你的對象是那樣地動人。如果說表現手法做得很好的話,當然本身也是一個相當動人的東西,那會比劇情片還動人,因為是很現實的東西,它不是劇情片可以用想像或捏造出來的。
當然紀錄片有它的侷限沒錯啦。有時候看劇情片,你會覺得:「哇!」它那個想像力之廣、之大,可以讓完全不是真實、現實的東西呈現出來,紀錄片不行,它還是要有一個現實東西在那裡,所以它有極限。可是當你找到正確的人或主題,然後能深入或長期追蹤,你拍出來的動人,跟劇情片是不一樣的,它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東西。
備註
- 張照堂訪談,訪問:林木材,逐字稿節錄整理:劉安綺,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時間:2015.11.11。延伸閱讀:林木材,〈不再遺憾-張照堂的紀錄之旅〉,《歲月.定格-張照堂》,台北:北美館,2017年2月。
- 《王船祭典》配樂Ommadawn Part 1收錄於麥可.歐菲爾德(Mike Oldfield)1975年發行的專輯Ommadawn。此專輯僅分為Ommadawn Part 1與Part2/On Horseback,各佔據唱片的一整面。
- 《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為胡台麗導演1983年於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攝製的人類學紀錄片,記錄排灣族部落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祭儀-迎送神祖之靈的「五年祭」(Maleveq)。本片也是台灣第一部有聲的民族誌紀錄片。